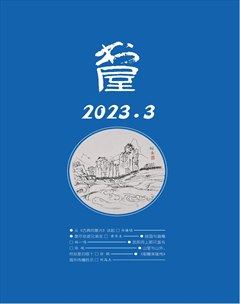1972年10月初,画家陈子庄携门生刘炳贤从成都东门九眼桥汽车站乘长途客车,沿府河南行,经中兴场续行二十里,抵达府河边苏码头(正兴场),与早一天到达的弟子陈滞冬、萧金平会合,师徒四人开始沿河看山写生。
府河以流经成都府得名。岷江自都江堰宝瓶口一分为二,内江流入成都腹地,析出柏条河、蒲阳河、清水河等支流,后在成都市区形成“二水抱城”的格局,在合江亭汇入府河。府河也叫濯锦江,最终在彭山江口鎮与经温江、崇州、新津流来的外江(金马河)汇为岷江干流。府河与金马河下游大片流域,汉代属犍为郡武阳县辖地。当地人把这一段府河叫武阳河。文献记载,武阳故地是最早的茶叶集散地。西汉辞赋家王褒写《僮约》,有“烹茶尽具”“武阳买茶”等句,此为我国饮茶、买茶的最早记载。
人类择水而居,河流即文化走廊。府河从成都开始,至彭山江口镇这段水路,是自成都府(益州)出川的最佳途径。自古以来,通过府河进出成都的文人墨客络绎不绝,如文学家扬雄、司马相如、李白、杜甫、苏东坡、黄庭坚、陆游、杨慎、巴金、李劼人等,画家黄筌、吴道子、李思训、徐熙、文同、齐白石、黄宾虹、张大千等,留下翰采文华,一江风流。
子庄先生选择武阳河写生,以苏码头开笔,观山高水远,感废兴成毁,写人伦风情,莫非有文化启蒙之意?
一
1972年正是陈滞冬拜师学画的第四年。
滞冬七岁那年,随父母被迫迁出如是庵的自家小院,搬到一个大杂院,与周遭环境格格不入,“忆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黄犊走复来”,当然,他绝无胆量效杜甫去打邻家枣树。到了“文革”之始,成都文化宫中学初一学生陈志东无学可上,结识了班上一萧姓同学的哥哥萧金平,一个戴深度近视眼镜的职业木工,随他走进一条萦纡的花径,知道了王国维、罗振玉、陈寅恪等人及其著作;认识了精通文史的刘静生、长于考古与道学的王家祐。尤为难得的是得以拜门画家陈子庄。
得英才而教,清高孤寂的子庄先生也拾取一段良缘。滞冬曾谈起第一次去江汉路37号拜见恩师的情景:“他本来早已不收学生,但接谈之下,知与我父母熟识,在四川省政协开会时,还与也是省政协委员的我母亲同在文艺组,于是才破例答应下来。此事直到一年之后,我父母设家宴专请先生当面拜托,我与他的师生关系,才最后确认。”
子庄先生是“在盐水里腌过三次,在碱水里煮过三次,在清水里漂洗过三次”的达人。他就像其一生崇拜的八大山人、任伯年、吴昌硕等,疏离庙堂,弃绝功利,一心侍弄笔墨。于是,诗、书、画、印与世迥异,呈现“简淡孤洁”的“平淡天真”。
拜师子庄先生,不徒学丹青艺事,还学到一种不趋时的生活态度和慢下来的生活方式,就“像一条小鱼,在生活的湍流中找到了一些可以生存的夹缝”。经恩师提议,大名“志东”改为“滞冬”,是年十七岁。
1969年1月18日,陈滞冬下乡插队仁寿县籍田区红花人民公社,“半个月以后,我独自一人跑回成都,一边仍和社会上那帮朋友厮混,一边抽空看书、画画、练书法,一有机会,就跑到陈子庄先生那里去看他画画,听他引古证今,谈艺术,论世人……我极少干农活,开始时在乡下时候多,城里时候少,后来渐渐城里时候多,乡下时候少,最后干脆待在成都,根本不去乡下”。
师傅带徒,不像课堂授课,照本宣科,增加知识量,而是竖立精神标杆,指明方向方法。如孔子言,从夫子游,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游着游着,小鱼就成了大鱼。“陈先生通常上午作画,午饭以后常常出门,或去街头茶馆喝茶,或去拜访朋友,或去公园写生。当时陈先生心脏病的症状已很明显,出门时常坐在我的自行车后架上,由我推着走。那几年时间中,我们几乎无日不见……我们常常边走边谈,当然更多是我听他谈艺术,谈他从前的经历,评论古今画家得失,谈文学与历史”。
二
清早,师生四人从借宿的正兴磷肥厂职工宿舍的机器轰鸣声和氧化硫的刺鼻异味中醒来。早饭后离开苏码头,迎着河上薄雾、远丘晨曦,有说有笑,不舍江岸。武阳河曲折蜿蜒,时路断江渚,有舟人野渡垂钓,遂买舟过江,复踏行莎径竹林,且行且停,道路又伸向渡口,再寻舟过渡,如此往复,不觉来到胡家坝(永安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