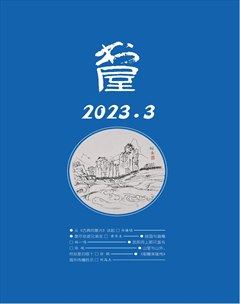大山既是一个自然概念,也是一个文化象征。很久以来,大山里代表着封闭、保守和落后,而走出大山则代表着走出封闭、保守和落后,走向现代文明、走向新的天地。这种集体无意识至今仍在人们的头脑中延续,去问问大山里的孩子,包括他们的老师,有几个不渴望走出大山,走向更广阔的世界?与此相对,又有多少城市孩子愿意走进大山生活?不过,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在现当代作家笔下呈现出不同的文学思考,有的认同山里(乡村)的生活方式,有的赞美山外(城市)的现代生活,也有的在山里山外之间深入思考,难下定论。笔者在重读了或初读《边城》《哦,香雪》《傩面》三篇现当代小说之后感想颇多。三篇作品创作时间相距八十多年,这八十多年是中国社会由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转型的时期,三位作家的价值取向和情感取向表现了不同时代中国人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精神动态。
一、《边城》:山里世界岁月静好
关于《边城》的评论文章不计其数,但有些作者比較专注于文本解读,而对作品的时代背景和沈从文的价值观关注不够。我认为,读懂《边城》内蕴,必须“重返”作者创作时的那个古老与现代碰撞的特殊时代。
《边城》创作于1933年,此时鸦片战争过去将近百年,距离新文化运动开端已有十多年,以工商业文明、城市文明为标志的西方现代文明不断侵入和影响中国。对于西方现代文明,中国人经历了由鸦片战争之后的被动接受,到新文化运动之后主动学习的思想转变历程。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西方现代文明对中国的影响从沿海到内陆,从城市到乡村,就像巨大的涟漪逐渐向四周扩散。即便在沈从文故乡偏远的湘西,也能感受到现代文明的鲜明印记,但西方现代文明与中国的传统文化之间存在巨大的“文明的冲突”。作为外来的强势文化,西方文明具有明显的“侵略性”,处于攻势,中国传统文化处于守势。但当时大多数现代知识分子对现代文明是心向往之并热情欢迎的,他们认为现代文明是启蒙国人的精神之“药”,而以乡土文明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几乎与蒙昧落后画等号。在现代文学作品中,“乡下人”大多是落后、愚昧、麻木的代名词,是需要启蒙的群体。
自称为“乡下人”的沈从文,曾先后置身于北京、上海、青岛等大城市,亲身感受了现代文明的影响,目睹了现代文明的利弊。与当时大多数知识分子不同,沈从文对现代文明的态度并非一味热情向往,而是抱有怀疑的。他在《〈长河〉题记》中曾这样写道:“去乡已经十八年,一入辰河流域,什么都不同了……最明显的事,即农村社会所保有那点正直素朴人情美,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在《八骏图》《绅士的太太》等小说里,沈从文对现代文明的标志性群体——大学教授给予了无情嘲讽,都市文明人用文明的绳索无形地捆绑自己,以至于坠入并不文明的怪圈里。而《边城》所描绘的环境和人物与之形成鲜明的对比,翠翠、外祖父、天保、傩送、船总顺顺等普通的边城人物构成了一个和谐宁静的世界,虽然那里也有人间的忧伤、死亡和悲剧,但湘西边城人代表着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显然,沈从文把乡村(山里)和城市(山外)看作两种对立的文明代表,前者代表传统文明,宁静、和谐、健康;后者代表现代文明,浮躁、功利、悖乎人性。当他对都市文明代表的现代性表示质疑,却又无法开出解决现代性弊端的药方之时,只能回首眺望湘西大山里的传统文明(农耕文明),投以深情的目光,赋予美好的情感和想象。他说:“这世界上或有想在沙基上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可那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这小庙供奉的是‘人性’。”沈从文将大山里的湘西边城描绘成和谐优美的世界,当然是心目中理想国的投射,有点类似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