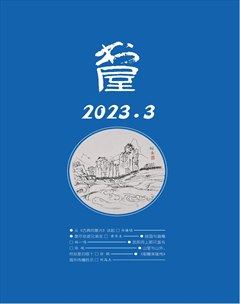香港大学黄心村教授的新著《缘起香港:张爱玲的异乡和世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以下简称《缘起香港》)令人惊艳。《缘起香港》一书的写作,缘起于作者在2020年张爱玲诞生一百周年策划“百年爱玲,人文港大”的纪念活动展览时的准备工作。黄心村教授通过港大档案馆故纸堆中的新材料,得以发现1939年至1941年间求学港大的张爱玲师友交往、文学阅读与学术训练的历史细节与详细面目。
书中讨论几位给张爱玲深刻影响的港大师长的章节,尤能显示出此书爬梳史料、探赜索隐的功底。历史教授佛朗士在课堂上让张爱玲形成了“历史的亲切感和扼要的世界观”,在现实中他也参与历史,与宋庆龄、廖梦醒、爱泼斯坦等一起组织保卫中国同盟,护送中国红十字会医疗物资北上,在港战期间加入香港义勇防卫军殉职,最后他化形成为张爱玲自传体小说《小团圆》中的安竹斯先生;中文教授许地山扎根港大,大刀阔斧地改革中文系,他对日常生活史的学术热情点燃了张爱玲对服饰文化的研究兴趣以及对微观细节的超常规执迷,并且蓄胡须、穿长衫的许地山教授还成了张爱玲小说《茉莉香片》中有着“特殊的萧条的美”的角色——言子夜的原型。
港大教授佛朗士、許地山与张爱玲有切实的师生接触,讨论他们与张爱玲之间的文化互动问题顺理成章,具有理论施力点和史料延展性。相较而言,《缘起香港》中讨论张爱玲私淑的一位被遗忘的英文世界文学家斯黛拉·本森的部分,更显研究者对一则文学史料问题“上穷碧落下黄泉”的求真精神。
1944年4月,将张爱玲奉为上宾的刊物《杂志》上有一篇《女作家聚谈会》的访谈录,这篇文字实录沪上知名女作家如张爱玲、苏青、关露、潘柳黛、汪丽玲等和女性文学研究者、记者等的对谈,一直以来也是张爱玲研究中相当重要的一篇文献。其中张爱玲在回应记者吴江枫“对于外国女作家喜读哪一位”的提问时,迤迤然回应道“外国女作家中我比较欢喜Stella Benson”,但张爱玲未及展开解释为何欣赏这位女作家,话题便陡然自动切换了。
黄心村教授敏感地捕捉到了这个留存于文字间的尴尬时刻:“她‘比较欢喜’的这位外国女作家似乎是个谜,没有任何解释,名字连中文翻译都没有。聚谈记录登载在四月的《杂志》月刊上,白底黑字,孤零零的一句话,几乎能够想象她说完后全场的静默无声,随后另一位女作家汪丽玲滔滔不绝开始谈她的最爱。”《女作家聚谈会》一文因记录了张爱玲讲述自己第一篇作品的来历、对同行女作家作品的点评、对古典文学作品的审美偏好、喜欢读的外国文学作品等内容,成为学界考察张爱玲文学发生学、解读张爱玲文学背景资源的重要素材,引用率一直颇高。可是偏偏长久以来,就是无人去深究文中这个张爱玲坦言很“欢喜”的、在当时连中文译名都没有的斯黛拉·本森究竟是谁。
《缘起香港》正面迎击了这个难题。通过细致的史料爬梳,我们才知道这位斯黛拉·本森竟并非无名之辈。她曾靠创作打入以维吉尼亚·伍尔夫为中心的“布鲁姆斯伯里”文学圈,尽管只能位处编外、不被看好;她曾嫁给一位姓安德森的男人,而这位安德森在她不幸去世之后续娶夫人并育有二子,即本尼迪克特·安德森与佩里·安德森;她书写环球旅行的游记《小世界》《世界中的世界》以及以自身经验为原型的小说,都显示出一种在当时颇为珍贵的不甚精英化的叙述腔调、平实却锐利的批评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