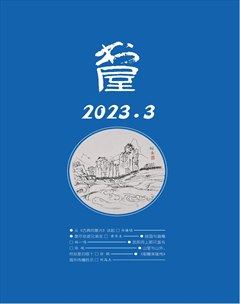一
鲍昌的《風诗名篇新解》出版于1982年,我是在古玩市场碰巧淘到的。这是本小册子,薄薄的,仅有二百一十八页,也仅仅对“风诗”中的二十四首“名篇”进行了“新解”。
我所感兴趣的自然是他的“新解”,看看具体“新”在哪里?
粗粗翻过,感觉他的“新”首先体现在他对这些诗题旨的解读上,确有诸多有别于他人的新说。有的令人眼前一亮,有的则令人顿生疑惑,或不以为然。再翻,发现他对每首诗的字、词、句的理解上,也有诸多有别于他人处。不过在我看来,倒是讲述得十分详细,即前人对某首诗是怎样诠释的,他又是怎样理解的。其实,也唯有如此才能彰显出他的“新”来。当然,这也是解诗的惯常路数。如果人云亦云,或炒些剩饭,那就了无价值可言了。
而我最感兴趣的当然是他附在每篇“新解”尾端的“新译”。在我看来,唯有他的“新译”才能体现出他对那首诗的整体把握或理解。在此或可打个不甚恰切的比方:这些“新译”几近于厨师最终完成的某道菜,并真真切切地呈给了食客(读者)。食客尽可通过对这道菜的观看及品尝来确定自己是否喜欢,是否合口味。至于前面对字、词、句的注释或解读,则相当于厨师烹饪那道菜的选料及烹制过程。对这一过程,有些食客可能感兴趣,有些食客可能不感兴趣,而那些感兴趣的食客或感觉味道不对、不适口的食客,自可去查看或追问该厨师具体是怎样选料及烹制的。
好了,闲言少叙,还是细细拜读他的这本小册子吧。下面便是他的一些“新解”以及我的部分“点评”。
二
他认为《葛覃》“从诗的内容看,诗作者或是一位少女。她刚在‘公宫’里受训结束,正在洗自己的衣服,准备回家去同父母团聚”。
实话实说,他的这一“新解”在今天看来已是几无新意了。现今解读《诗经》的人基本上都认为《葛覃》是首描写女子准备回家探望爹娘的诗,只是在个别细节上有些不同看法。诸如该女子究竟是在“‘公宫’里受训结束”时准备回家的,还是在某大户人家“采葛制衣”时想起父母的。但这皆无关宏旨。当然,他所说的“新解”,自是针对《毛诗序》等所认为的此诗是讲“后妃之德”的。我认为他的这一“新解”很有“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意味,就是把《诗经》从“经”的神坛上拉下来,“让民歌回归民歌”。
他认为《兔罝》“是以诸侯田猎活动为背景,歌颂诸侯的武士之歌”。
我认为他的此“新解”无甚新意,传统的说法大致都是如此,或大同小异。而我已故的老师高鹤声先生则认为,《兔罝》是首讽刺诗,讽刺当政者对民众的防范、钳制等。
他认为《汝坟》“是一首反映出普通人民反战情绪的诗”。对此他解释道:“本诗中的‘君子’可能是个普通的庶人。他出外服役去了,因此诗人怀念他,‘惄如调饥’。但诗中的次章明明写道:‘既见君子,不我遐弃’,那就是说,这个出外服役的人跑回来了。为什么跑回来了?诗中并未明确交代。但在本诗的卒章中,却透露出一点消息。卒章诗句的语气,既像是诗人本人的,也像是跑回来的‘君子’的,表明了出外服役的征人对王室的厌憎,也表明他对战争动乱的反感。”
他的这一“新解”我是碍难认同的,他的相关解释在我看来也太过牵强。我认为《汝坟》是首少女吟诵的情诗。《汝坟》中有句“王室如燬”,其中的“王室”通常被释作“王之宫室”,“王室如燬”自然就是“王室像大火焚烧一样”了,他也是这样认为的。而流沙河认为,“王室”其实就是“大房子”。流沙河坦言:“迄今为止,本人是第一个把‘王室’解为‘大房子’的,而‘大房子’……就有一个公房,就供他们男女在里面自便。”流沙河的理解确实新颖,不过在我看来,将这个“王室”释作这位热恋少女的“心室”或“心房”,或许更为恰切。
他认为《麟之趾》“是古人应用于现实生活中的一首婚礼歌曲,或议婚时的贽礼歌曲”。
这样的“新解”固然不能说错,却也只能说是“一家之言”。而高鹤声先生则认为,《麟之趾》是首讽刺诗,是用反讽的口吻在揶揄那些“贵族子孙”。
他认为《殷其雷》“是一首周代普通人民为了抗议沉重劳役压迫而唱出的逃亡之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