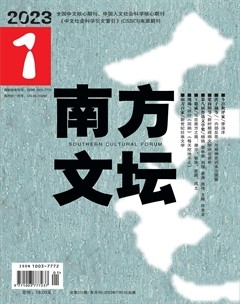年逾九秩的著名文学评论家阎纲先生,从事文艺活动已经有七十多年的历史了。他直到现在仍然笔耕不辍,还出版《我还活着》散文集①。新时期是阎纲“评论人生”的高光时期,他一直身处文学现场,发表了许多重要的作品评论,坚定地为新时期文学发声与护航。与此同时,他还不断呼吁加强文学评论力量,编辑出版评论丛书,促成《评论选刊》诞生,为新时期文学评论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发出“在场者”的评论声音
从1949年至今,中国当代文学走过了七十多个年头。作为文坛的“常青树”与“在场者”,著名评论家阎纲先生一直与当代文学同行。“在场”是西方形而上学体系内部“存在论”问题的一种概念表述,是指“存在呈现于此时此刻(当下时刻和当下场所)”②,强调的是空间与时间上的当下性。阎纲退休之前长期在《文艺报》《人民文学》《小说选刊》《中国文化报》等文艺报刊从事编辑工作与评论工作,因为身份的特殊性,他见证了当代文学的许多重大事件,参与了许多重要作品的争鸣与讨论,对当代文学的发生与历史进程都有着直接的感受与经验。从这个意义上讲,他就是中国当代文学场域的重要“在场者”。
1950年,年轻的阎纲在家鄉陕西礼泉县开始了文艺宣传工作,并在1951年出席陕西省首届文艺创作者代表会议并领取奖项。1952年,阎纲作为“调干生”考入兰州大学中文系,系统学习文学专业的理论知识,为以后的评论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56年,阎纲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中国作协,进入《文艺报》从事编辑与评论工作。1961年底,阎纲与王朝闻、李希凡、侯金镜等评论家在《文艺报》上对《红岩》进行过系统评介,他还在1963年出版过《悲壮的〈红岩〉》一书。应该说,“十七年文学”期间,是阎纲“评论人生”的起步时期。正是因为长期“在场”,阎纲才能深刻认识、准确把握当代文学的发展进程。
1975年,阎纲结束了干校生活重返文坛,参与《人民文学》复刊工作,并担任编辑。“文革”结束后,文坛乍暖还寒,思想解放还未全面展开,《人民文学》发表了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班主任》发表后,招致诸多反对、批评之声。阎纲在《班主任》遭受非议的时候,站出来撰写了《谨防灵魂被锈损——为新作〈班主任〉叫好》,进行评介与支持,称《班主任》正是“提醒人们严肃注意孩子的彻底解放的问题,能不激起家庭、全社会、教育者、受教育者的滚滚思潮吗?”阎纲坚定地为“正视现实生活,勇于提出尖锐的社会问题,不落俗套的《班主任》拍手叫好”③。《班主任》作为“伤痕文学”的开篇之作,其引发的反响与思潮在当代文学史上具有非凡的意义,这与阎纲等评论家们的支持与阐释也有直接的关联。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全国第四次文代会的召开,标志着新时期文学的到来。新时期是思想解放、人性复归的文学时代,文学迎来了勃勃向上的黄金时代。随着《文艺报》的复刊,阎纲重返《文艺报》担任编辑工作。阎纲许多重要的文学评论文章,均写于这一时期,如《不妨解剖一个——论“写真实”》《“高尚的圣者和殉道者”——读〈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小说出现新写法——王蒙近作》《〈灵与肉〉和张贤亮》《为电影〈人到中年〉辩——对〈一部有严重缺陷的影片〉的反批评》等。这些文章对应着当时的作品争鸣,这不仅说明阎纲是“在场的”,也说明阎纲作为“在场”的评论家参与、触发乃至引领了当时的文学思潮。
1979年由《人妖之间》作为导火索引发的“写真实”的争论,正是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文学思潮争论的焦点。伴随着思想解放,1950年代、1960年代关于“写真实”的讨论又开始重新被关注与评估。“‘写真实’无疑成了新时期中国文学界最热门的话题。”“多数文章肯定了这一口号的正确性,否定了过去对这一口号的批判,指出这是现实主义的核心。”④阎纲在文章《不妨解剖一个——论“写真实”》中讨论什么是“写真实”,讨论“真实”的标准,指出:“真实不真实,实践出真知”,进一步提出:“认识表现为曲折的实践过程,文艺创作亦复如此。”号召文艺界,“把有尖锐争议的作品提出来大家公开讨论”⑤。这些观点为当时“写真实”的讨论提供了颇具价值的意见,也可以看出阎纲敏锐的洞察力与对文艺思潮的精准把握力。
阎纲正是秉持现实主义“真实性”的理念开展文学评论,发掘优秀作品,为有争议的作品发声。中篇小说《犯人李铜钟的故事》是阎纲发现并极力推荐的作品。这部短篇小说在发表之初,也没有逃过和《班主任》一样被批判的命运。阎纲第一时间站出来,撰写了《“高尚的圣者和殉道者”——读〈犯人李铜钟的故事〉》为其鸣不平。称赞小说中的“李铜钟”是普罗米修斯式的人物,同普罗米修斯一样都是“最高尚的圣者和殉道者”,称这部作品“恢复了我国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认为它的价值在于“作者具体写时,怎样把‘真实’和‘崇高’艺术地结合起来”⑥。阎纲在评论张贤亮当时颇有争议的作品《灵与肉》时称:“他念兹在兹的,是恩格斯的话:‘真实地描写现实关系。’比之一般的‘伤痕文学’来,他更忧愤深广。”“张贤亮所操的现实主义,无疑是深化了的。”⑦同样,在为电影《人到中年》作出辩护性时,阎纲评论《人到中年》:“为歌颂而暴露”,并由此指出:“直面人生,正视社会矛盾,实在是发展文艺创作的必由之路。”⑧他关注王蒙具有意识流色彩的新作《夜的眼》《布礼》《风筝飘带》《春之声》《海的梦》《蝴蝶》,准确地概括出王蒙新作是一种方法上的借鉴,认为王蒙新作是“现实主义的新品种,并没有告别现实主义的几个真实性的要求”⑨。举此重要几例,可以看出在新时期文学之初,在坚定的现实主义文学立场下,阎纲既有作为一个评论家所具备的敏锐目光,又有敢于发声、敢于引领文学潮流的胆识。
阎纲文学评论的语言也非常有特色。对于具体作品的评价,阎纲总能通过犀利、简洁且富有诗一样澎湃的语言,对作品进行敏锐、生动、精确的评论判断。他评论小说《犯人李铜钟的故事》时,这样辩护:“嗟呼!已诺必诚,不忧其躯。壮哉!真正共产党人的侠风义气!”⑩同样对于高晓声系列小说中的人物“陈奂生”,阎纲评论道:“陈奂生终日劳碌,半生清苦;忍气吞声,逆来顺受;时来运转,受宠若惊;眼花缭乱,呆头木雕;好心办事,事与愿违。世道大变,人情难测,一身清白的农民,掉进‘关系学’的五里云雾。”11这都展现出阎纲文学评论生动、鲜活的语言特色。刘再复在评价阎纲的评论风格时说:“在历史转变时期,文学更需要感应的神经、攻守的手足,更需批评的生气、活力和战斗力。”“新时期文学是在清除极左的血污中开拓自己的道路的,它首先要赢得生存和发展的权利,它需要不带学院气的犀利的‘时文’。”12白烨对阎纲的评价亦如此:“他引人注目的是:仗义执言,不避锋芒,义愤中深含识见;实话实说,不落俗套,平朴中自有文采。他把真情与诗意揉成一体,带来了一股清新引人的文评新风。”13就连阎纲自己总结对文学评论的要求时也认为:“唯八股之务去,行文体之改革,引诗意和真情入文,推倒呆滞生硬的评论之墙。”14这都是其文学评论富有活力与诗意的原因所在。我们可以看出,新时期之初,倘若没有阎纲这些激情且富有战斗性的文学评论的挖掘与阐释,很多优秀的文学作品可能会被埋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