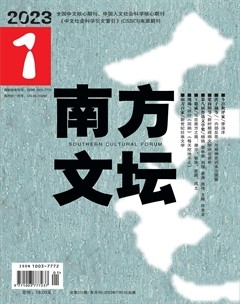李浴洋是我的师弟。不过我博士毕业的时候,他还没有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我是后来在北京市社科院工作的时候,才有缘认识他。最初是因为北京市社科院图书馆的资源非常有限,经常需要麻烦师弟师妹帮我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借书或复印资料,就经由介绍找到了他。劳烦他一两次之后,发现他非常能干,而且效率极高,总是第一时间就完成任务,心想这确实是一个“靠谱”的师弟,也就心安理得地把这份差事交给他了。
浴洋办事干练,考虑周全,在认识他的师友圈里可谓有口皆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2015年秋天,博士二年级的他在北大中文系的资助和支持下,召集和组织了“时代重构与经典再造——博士生与青年学者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我读博的时候,由博士生来办学术会议几乎闻所未闻,何况是如此大规模的一次盛会。两天的会议,与会者差不多在一百人上下,快结束的时候,又专门邀请了退休的孙玉石老师来做演讲,把这次研讨会推向了高潮。这可以说是他在学术界的初试莺啼,取得了很好的反响。此后,浴洋一发而不可收,又策划和组织了一系列的学术活动,包括各种类型的研讨会和座谈会,也包括为学术刊物就某一专题组稿,平均每年都有三四次。我自己参加的,就不下十次,经浴洋之手发表的笔谈或论文,也有十几篇。
我与浴洋的合作,最持久且仍在进行中的是经营“论文衡史”学术公号。2016年6月公号创办后,有一段时间基本上是我独立编辑。翌年3月,浴洋加盟,专门负责每周一次的书讯栏目,帮我分担了很多工作。浴洋做事非常得力,总是提前就把内容准备好,编排得井井有条。这不只是一份技术性的劳动,选书本身也见出浴洋的学术眼光。他主持的书讯栏目,不仅为用戶(包括我在内)提供了最新的学术信息,也开拓了他们的眼界,成为“论文衡史”公号标志性的品牌。2021年冬天,我和袁一丹分别出版了《新文化的位置——“五四”文学与思想论集》和《另起的新文化运动》两本著作,浴洋主动提出办一场小型工作坊,围绕两本新书,就“五四”新文化研究的学术传统与可能性这一论题,邀请年轻学者一起座谈。在浴洋的操办和主持下,“新文化的射程——历史综合如何可能”工作坊在北京中间美术馆顺利进行,我也再一次见识了浴洋办会的才干。
学术活动的召集、组织和运作,不只需要处理事务的长才,更考验主持者的学术趣味、判断力乃至前瞻性。浴洋在后面这一方面也表现出色,他对话题和主题的选择,都包含了自己深入的思考。即以“时代重构与经典再造”这一主题而言,浴洋意在中国现代转型的大背景下,通过“经典”的升沉起伏这一独特的视角,探讨现代思想与文化的重构,这其中显然包含了一种学术史的视野。自读博时起,学术史就是浴洋关心的核心问题之一,他组织的诸多学术活动,大体都包含了这一面向。更重要的是,在浴洋那里,学术史不仅是研究的对象,也是一种实践的方式。无论是他策划或协助召集学术研讨会与座谈会,还是在报刊上组织专题的评论或笔谈,还是对当代学者的深度采访,都是在参与建构当下活的学术史,对此浴洋显然有着充分的自觉。
这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浴洋做的学术访谈。自2016年起,浴洋先后为孙玉石、洪子诚、陈国球、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吴晓东、王德威、黄子平、陈平原、王润华、贺桂梅、孙郁等多位学者做过访谈,从这份名单不难看出,他们中大多数是北大中文系或有中文系背景的老师,还有几位任教于海外,但都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这些访谈多围绕被采访者的著作或某一具体的研究领域而展开,然而都包含了他们对学术历程的回顾和对治学经验的总结。在这个意义上,它们本身就构成了中国现当代文学这一学科的鲜活的学术史文献,必将为当代和未来的学术史家所珍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浴洋的工作,就没有这些文献,他投入大量的心血,为我们这个学科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
做学术访谈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它不是漫无边际的闲谈,需要访谈者预先做足功课,有充分的准备。我有幸参加过一次这样的访谈,那是2017年10月,王德威和陈国球两位老师来京开会,浴洋邀请我跟他一起,与两位老师就《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撰进行对谈。此前浴洋已经向王德威老师推荐我参与该书中文版的翻译工作,我也非常高兴能有机会与两位老师当面交流。那天下午,我和浴洋来到北大博雅国际酒店王德威老师的住处。稍微寒暄几句之后,我看到浴洋拿出几页打印好的纸,上面是他为这次访谈准备的采访提纲,我才知道他下了多么大的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