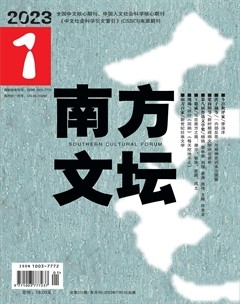因参加第八届鲁迅文學奖文学理论评论奖的评选活动,较为系统地阅读了一百六十一部(篇)参评作品,这些作品都是最近这四年间发表、出版的;加之评选期间十一位评委之间的意见交流和思想碰撞,触发了我对新世纪以来的文学批评和评论的相关问题产生了一些感想和思考,行诸文字,与同仁们交流。
一
文学批评和评论在今天已经成为问题。何以文学批评和评论,在今天会成为一个问题?估计很多评论家在从事文学评论时,是不太会多留意这一问题的,但在集中阅读完参评作品之后,这个问题似乎会不断地浮现出来,原因在于很多属于学术研究的文章和论著大量涌入鲁迅文学奖的参评系列,文学批评、评论与学术研究是不是一回事?站在文学批评和评论的角度看,这似乎是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理论层面,大家都明白文学批评和评论需要学术学理的滋养,但两者之间毕竟不是简单的等同关系。与新世纪之前的文学批评和评论相比,学术味儿在今天的文学批评和评论中较之以前是明显增强了。如果说“新时期”的文学批评是浮躁凌厉、拨乱反正和直抒胸臆,那么,经过20世纪90年代的“思想家淡出、学问家登场”的历史洗礼,学术味儿弥漫到整个文学批评中来,到今天可以说随处可见、无处不在。不仅学院中的教授、博士生占据了文学批评作者队伍的绝对多数,而且很多学术研究课题直接参与到文学批评中来。一些原来作协系统的评论家,改变自己的评论风格,行文上也在向学术研究方向靠,以显得有点学术根基。尽管现状和批评的风气如此,但我以为在思想意识上还是应该明确文学批评、评论与当代文学的学术研究之间的区别,两者并不完全相同。文学批评和评论比较多地着眼于文学的当下问题,对一些文学史上的作家作品的论述,当代文学批评和评论有时也会涉及,但着眼点还是当下的文学状况、文学面临的问题,并且是以评为主,与当下的文学创作有着直接的关系。有些评论借题发挥,借文学史上的相同和相似的问题来发挥批评家自己的看法,但着力点离不开当下的文学问题,而不是一头栽进历史问题研究中去。譬如,90年代王元化先生论样板戏的文章,他的着力点是针对当时社会上有些人为样板戏翻案,把样板戏的实践捧得非常高。王先生结合“文革”历史和京剧艺术特点,对京剧以及中国传统戏剧的改编,发表了自己的意见。王先生的这些评论不是单纯的京剧研究,而是当代文艺评论,是针对着当代文艺创作中存在的某种思潮、现象和倾向而发的。如果对照后来这些年舞台上出现的《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杜鹃山》《沙家浜》的粉墨登场,以及戏曲创作中大量以样板戏为蓝本的新编戏曲创作取向,再参考一下王元化先生90年代的一些批评意见,或许会感到他的某些意见具有超前的预感。这种预感,或许就是文艺批评的敏锐与洞见。还有像文学批评中有关人的问题的论述,这是自“五四”以来新文学运动中最有力的理论建构和批评总结。陈独秀、胡适、鲁迅、周作人、茅盾、郑振铎等曾经倡导的“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形成了一种新的传统。这一传统近百年来,始终影响着中国作家和文学批评家的创作、评论,尤其是经历了“文革”的坎坷之后,“人的文学”在观念上受到普遍重视,“新时期”以“文学主体性”的理论面目,影响着创作和批评,成为这一时期的文学主潮。80年代中后期,文学批评有“向内转”的说法,主张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要从关注外部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现象,转向对人的心理、情感和语言结构、潜能的关注。文体实验是“新时期”文学由外向内转向的一种文学探索。在莫言、王安忆、韩少功、马原等一批作家作品中,这种转变非常明显。年轻的余华、苏童等南方作家的实验文学尝试,以新历史小说的虚构、想象手段,将人们的视野延展到民国、“文革”时期,形成了与以往现实主义审美传统并行的另一种文学叙事样式。这一时期一批“青年批评家”的文学批评和评论强势引领和助推这股实验文学的审美潮流,《上海文学》的理论栏目以及《读书》《当代文艺思潮》和《当代文艺探索》上的评论文章,给人以强烈的在场感。“青年批评家”以各自独特的批评语言,表达着自己对“新时期”文学实验的种种看法。作家与评论家之间不是谁听谁的关系,而是同步共建时代的文学场域。较为典型的案例就是《上海文学》编辑部发起的杭州“西湖会议”,有很多评论家、作家自由讨论,发表自己的作品。90年代之后,中国文学批评进入到了“后新时期”,体制在新的规范下重新发挥作用。作家不仅大量进入市场,也大量进入高校体制内;文学批评的发表被要求学术的规范化、格式化,甚至还出现了核心期刊、非核心期刊和扩展版之类的等级阶梯。新世纪之后,评论文章很多都愿意挂上学术的徽标,一些评论文章的页下都注明某某课题的阶段性成果等文字,这已成为中国新世纪文学批评最奇特的文体景观。如果说新世纪学术研究对于文学批评、评论是一种全面的进入状态,那么,进入之后的溢出效应或许就显得错综复杂、一言难尽。学术昌盛之下的文学批评自我意识的相对减弱,不能不让人关注到学术研究与文学批评之间的差异问题。这是新世纪文学批评发展过程中面临的突出问题。如果要问,此次鲁迅文学奖评论奖评选与以往有什么不同?或许作为学术研究课题的文学批评和评论的数量之多,是以往评奖中少有的。这些学术课题,放在学术研究的系列中,有些可能是不错的成果,但对于当代文学批评和评论来说,未必是最突出的表现,因为文学批评不要求这么系统论述,将问题的来龙去脉从头到尾事无巨细地述说一遍,这是书斋里学者做研究的典型做法。学术研究要求研究者对研究对象全面占有,越丰富越好。所谓学问、学养,最重要的标志之一,是知识渊博,史料丰富。但文学批评似乎对这种系统性、全面性、学术性的要求没有那么刚性,文学批评首先推崇的是批评家对作家作品的敏锐的感受力和准确的判断力,所谓灵魂在杰作中冒险,是对文学批评特征的一种简明概括。20世纪批评史上,李健吾的《咀华集》《咀华二集》被誉为印象批评的杰出代表,凸显的是作者对文本的直观阅读感受和明晰的判断能力,批评家与作家作品之间,几乎是零距离接触,身处同一环境氛围,甚至有时面对的问题和对象是彼此熟悉的。在这种情况下,文学批评的话语建构,不仅触及作家的敏感神经,形成某种语言霸权;而同时,作家的批评反弹,也会促使文学评论家修整和调整自己的话语形态。像李健吾当年受到巴金、卞之琳的反批评之后,发表了《刘西渭先生的苦恼》,除为自己的批评辩解之外,此后改变了对曹禺、巴金作品的否定性批评,在评论文章中尽可能挖掘这些作家作品的积极意义和正面价值。后人撰写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中,常常为李健吾的这种变化感到惋惜,但很少有人将李健吾的这种批评变化与批评家参与同时代的文学建构所遇到的具体问题结合起来考虑。文学批评受外界和时代等因素的影响而有所改变、调整,这是以往文学批评中经常遇到的情况,在今天也依然如此。如果把最近这些年的批评和评论文章集中起来看,可以看到有的作家作品前些年评论不多,而最近一些年讨论多起来了。可能是一些评论家觉得以往的评论对这些作家的作品谈得不够到位、不够透彻,需要进一步阐释和发挥。这样的批评调整,也属批评常态,批评史上对某些作家作品的评价随着时间的流逝,前后有变,那都是有的。只是有的变化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有的变化只是批评家个人意见,说说而已。除对既已成名的作家作品的评论之外,文学批评应该有所拓展,尤其是对文学发展的多种可能性问题,提供前瞻性的看法,具备超前的观念和理论。但目前所能见到的批评文章,对于新的可能性的理论探讨似乎有所不足。一个阶段相对集中的文学批评的话题和问题意识,通常都能反映出一个阶段文学批评受时代因素影响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