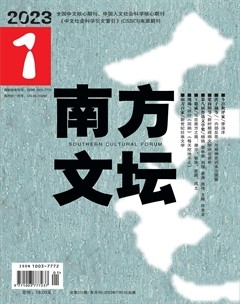鲁迅文学奖四年一届,参评作品中的多数,也是近四年来的新作。但要更好地评价、把握这些新作,仅仅关注最近四年的实绩肯定是不够的,某种更纵深的、更深长的视野,应该不可或缺。因为,新的文学地貌的生成,有时要依靠断裂、崛起、不同板块间的剧烈碰撞;更多时候,则是文学史内在运动趋势长期演进、沉积的结果。仅就诗歌奖而言,这次参评的诗人不少都有三四十年以上的写作积累,甚至曾是当代诗歌剧烈“造山”运动的发起者、推动者,这也为“长时段”的观察提供了可能。
2022年7月,长江诗歌出版中心为臧棣的新诗集《世界太古老,眼泪太年轻》组织了一次线上的研讨,当时臧棣的一段自述,很可以在这里引述:
我属于“60后”这代诗人。这代诗人经历过当代中国很多的重大的历史事件。当代中国社会的剧烈转变,也促成了当代诗歌的大起大落,并导致当代诗歌的内部关系特别多样,特别丰富;进而也影响到当代诗歌的脉络的复杂性。这些都是很独特的背景。韩东去年在《青春》杂志上编发我的一组诗时说,我的诗里有当代诗歌发展脉络的很多印迹。①
在當代诗歌的“复杂脉络”和“多样关系”中,臧棣和韩东“占位”不同,曾是不同诗歌趋向的代表。如今,两位60后诗人惺惺相惜,并非出于一般的诗歌友谊,更多还是当代诗歌“大起大落”之后“同时代人”对过往历史印痕的共同感知。
一个多月后,臧棣和韩东双双获奖。这两位60后先锋诗人的获奖,可能是本届诗歌奖的最大亮点,对于观察当代诗歌的来踪去迹,也有指标性的意义。特别是在延展原有写作脉络的同时,两位诗人近年来的写作都发生了一些潜在的新变,当代先锋诗歌整体的转化趋势也隐约显现其间。譬如,用素朴、冷峻的日常语风,刻写生活感知的细腻层次,是韩东一贯的风格,获奖诗集《奇迹》自然延续了这种风格,不动声色地写动物、人事,聚焦日常生活的诸多平凡。不同的是,韩东当年的不动声色,总会蕴含某一种叛逆、对抗的姿态:对抗陈旧的文学传统、对抗僵硬的意识形态、对抗平庸乏味的社会伦理。这样的姿态并不总是高亢的,往往伴随了先锋文学中常见的人和世界之间的疏离感、倦怠感。读者和批评者都注意到了,《奇迹》中的诗人已变得更温和甚至慈悲了,不是站在生活的一侧去观察、冷讽,而是更多倾向于安心于生活的内部,去关切死亡、亲情、离别,去体知平凡生命的脆弱和庄严。韩东的语言还是节制的、散漫的,但如日间的光线,具有了某种暖意、某种纤弱又不失广大的揭示性,让人读后久久回味。同样,这样的“变”与“不变”,在臧棣的诗中也有表现。在当代诗人中,臧棣大概是产量最高、出版诗集最多的一位。在他庞大的诗集序列中,获奖的《诗歌植物学》具有某种的总结性,在“博物”的视野中将他擅长的“博喻”想象力发挥到了极致。更值得注意的是,以“植物”为对象的写作,已脱出一般“咏物诗”的模式,更多是要以“植物”为友:不是将花卉、草木、蔬菜作为“我”观察的客体,而是看作是亲密相伴的家人、友朋。由此一来,精湛的语言技艺所要彰显的,不完全只是“心灵的骄傲”,按照好友西渡的解读,而是“我”与植物之间、我与世界之间“互为主体”的关联。②
不准确地说,两位先锋诗人的“变化”印迹,具有一定的同步性,同样更为舒展、从容,有了一种与世界和解、与日常生活对话的趋势,也在一定程度落回到某些情感和文学主题的基本面。从年龄上看,不少60后已接近耳顺之年。这是否意味着当代先锋诗歌经过了热烈莽撞的年代,也已走向中年的开阔、甚或老年的成熟?抑或说先锋的动力已有所衰减、消退,需要在更宽广一些的伦理感受、生活感受中得到转换?如何观察、理解这样的变化,或许要作为一个问题看待。兰波曾说:“诗必须绝对现代。”在7月的线上讨论中,臧棣重申了对这一贯穿性原则的认同“就是要求现代诗要有一种包容、吸收,转化,更新事物的能力。一种自觉的创造力”、也就是“把自己的一大部分,交给未知的领域,未知的命运”。事实上,这一“现代”原则不仅贯穿了先锋诗歌的历史,放大一点看,同样也是中国新诗百年来内在的“引擎”,也由此塑造了新诗整体的美学风格、文化气质。借用20世纪30年代林庚的说法,“自由诗”(“新诗”)因要突破陈旧的感受模式,不断创造新的感觉、不断冲锋陷阵,“紧张惊警”成了它的特征和前提。珍视这样“现代”活力的同时,林庚又担心一味“紧张惊警”,自由诗会走上偏僻一途,失去了自身的公共性。他转而认为“格律诗”可以构成调和、纠正,因为“格律诗”具有可以普遍接受的形式,有了“普遍形式”的帮忙,能抵消“自由”的尖锐、紧张,为新诗带来“从容自然”的风度。从林庚的角度审视,“必须绝对现代”的当代先锋诗,经过了三四十年的滚动,它的某些动力在衰减,某些的视野和层次在打开,大概也是由“紧张惊警”而趋近“从容自然”了。在公众面前,先锋诗人还会延续历史的惯性,扮演一类文化“异端”的角色,可这个“异端”大概不会特别具有挑衅性了,在满足文化多样性需要的同时,也自我安稳下来,贴近普遍的、带了点沧桑感的人性。
厌倦陈熟、必趋于生新;厌生新者,又会返趋于陈熟。“生新”与“陈熟”的辩证,本来是文学生活的内在规律,“紧张惊警”与“从容自然”的分别,可从这个角度理解。但在林庚那里,“从容自然”还不只是一种风格,同时也和某种广袤、浑然的世界感、整体感相关。在他的表述中,“格律诗”也是一种“自然诗”,如宇宙一般均匀、包容,具有自然、谐和的形体。这样浑融的整体性、自然感,似乎是刻意求新、强调差异的现代诗所一向欠缺的。获得本届鲁奖提名的诗人阿信,在诗集《裸原》所附的诗论中,就针对这一点谈了自己的理解:
不容否认,百年新诗是汉语诗歌传统之上的一种再造。当代诗歌在处理纷繁复杂“现代性”经验时更是达到了汉语诗歌前所未有的精神广度和深度。但不容回避的是,当代诗歌在抵达语言的所有可能性向度的同时,也隐含着种种精神危机。其中之一就是遭遇着人类生存图景的变异,传统审美情境的消失。身处城市的诗人们的经验和想象力遭遇后工业时代消费主义文化的重重侵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