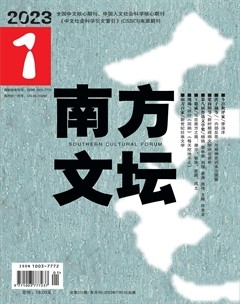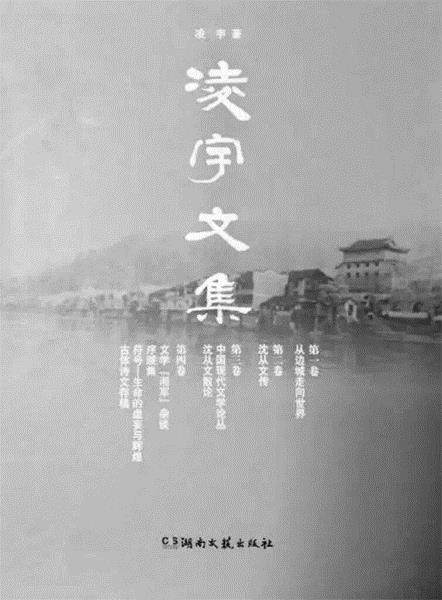
凌宇先生是沈從文研究的全国著名的专家。在20世纪末80年代初期,沈从文研究还是一个颇为敏感的研究领域之时,凌宇先生便像发掘文物一样,将沈从文作品从故纸堆中收集整理出来,并进行深入的研究,先后出版了专著《从边城走向世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版)和《沈从文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此外,凌宇先生还发表了一系列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沈从文研究论文,在学术界引起强烈的反响。可以说,凌宇先生对沈从文研究具有开拓之功,为后来的沈从文研究留下了广泛而深远的学术影响。凌宇先生除了在沈从文研究领域取得了杰出的学术贡献之外,他还对20世纪八九十年代湖南当代著名作家作品进行广泛而深入的研究,著有《重建楚文学的神话系统》(湖南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此外,凌宇先生还对《三国演义》的文化意蕴进行创新性的探讨,著有《符号—生命的虚妄与辉煌:〈三国演义〉的文化意蕴》(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2016年12月,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凌宇先生的四卷本《凌宇文集》,这可以说是凌宇先生大部分的学术成果的总结。凌宇先生之所以取得如此多的重要学术成果,是因为他辛勤的学术钻研的结果,这也与他的学术思想与学术方法具有紧密的关系。我以为凌宇先生的学术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坚持人文主义的学术立场与坚守“文学是人学”的信仰
凌宇先生坚持人文主义的学术立场,他在文学研究过程中始终关注人的生命,人的命运,坚守文学的使命,他从来没有动摇过“文学是人学”这一信仰,表现对人的存在的终极关怀,体现出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文传统和价值立场。凌宇先生曾经对于自己的学术生涯作了这样的总结,他说:“首先,坚持中国的人文传统的学术立场,对人的现实存在和终极存在保持着高度关怀。这点不仅仅贯穿在我的整个沈从文研究中,在对当代文学、古代文学的研究中也是始终如一坚持的一点。无论是我对沈从文文学世界中城—乡、苗—汉二元对立中人的悲剧性存在的解读,在当代湖南作家群尝试建构当代神话内蕴,对人的现实生存方式的质疑与浪漫主义理性追求的关注,还是在对《三国演义》的解读中,涉及对儒家伦理问题的历史追寻与当下思考,引发了自‘五四’以来对传统文化——伦理价值判断的反思,其间都倾注着一种人文主义的人生价值立场和属于我自己的生命激情。”①
凌宇先生的这一表述,为我们探寻其学术追求的人文主义立场具有重要的作用。他的沈从文研究就非常突出地体现了人文主义的学术立场。凌宇先生无论是在《从边城走向世界》,还是在《沈从文传》中,以及在对沈从文的人生经历的叙述中,都使我们认识到沈从文在“五四”思想启蒙下,生命从随顺命运的浮沉到决心挣脱命运的安排,自我掌握自己的命运,独立地支配自己,无论是“左”或右的思潮,也无法动摇他的人生航线,走着一条孤独的人生之路,奋勇向前。凌宇先生的这种叙述,就是从沈从文的生命出发,始终围绕沈从文生命的抉择与坚守这一人文主义的立场进行的。凌宇先生在对沈从文作品的分析评论时,也是坚持人文主义立场的。譬如对《边城》中翠翠、傩送之间的爱情的分析论述,就是从人文主义的立场出发的,他写道:“我们从翠翠、傩送身上,看到了沈从文笔下乡村世界的又一种生命形式。它内涵着勤劳、朴实、善良、热情,信守着自己的本来,在爱情、婚姻关系上,它表现为自然、纯真、健康;它又是自主自为的,抗拒着封建文明的污染,在关系到人生命运结局的重大问题上,它不同于肖肖辈的那种生命形式,处于被环境支配与左右的地位。它有主心骨,坚定地把住命运的航舵。”②凌宇先生揭示出翠翠、傩送抗拒外在的压力,敢于追求自己人生幸福的“自主自为”的生命形式,坚定地把握自己命运的航舵,这种人生形式便是人文主义精神的体现,这样,凌宇先生从人文主义立场对于《边城》的主题意蕴作了很好的阐释。又如,凌宇先生对于《丈夫》的评论,我们只要看一下标题《灵魂的战栗与人的尊严的觉醒——沈从文的小说〈丈夫〉读后》,就可以感觉到凌宇先生同样是从人的尊严的觉醒这一人文主义立场来进行论述的。凌宇先生在分析评论当代湖南作家作品时,人文主义的价值立场依然是他观察社会人生的重要原则。譬如对于孙健忠《醉乡》主人公矮子贵二的形象分析,就是从矮子贵二的觉醒与人的价值的确立来进行的,论文写道:“从贵二的崛起中,你不只是看到经济翻身的表层意义,而且深一层地发现了他的人的价值的重新确立。”“你没有简化人物精神转变的过程,而是真实地、极有层次地描绘了贵二自我意识觉醒缓慢得令人焦急的心理过程。随着这一过程的完成,贵二开始摆脱命运对自己生命的支配。”③再如,著作《符号—生命的虚妄与辉煌:〈三国演义〉的文化意蕴》中对于诸葛亮人生悲剧的论述,同样是从主体自我的视角进行论述的,指出诸葛亮“这种对伦理规范的高度认同,所导致的只能是对人的自我的严重压抑”,“主臣尊卑,从根本上决定了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无论诸葛亮具有怎样的经天纬地之才,都只能在这种尚未出仕便被预设的宿命式关系中施展,同时也宿命式地预定着诸葛亮这一类‘士’,无法真正成为历史的主角,也无法真正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④。可见,凌宇先生的人文主义学术立场贯穿于他的学术的始终,其中也流注着他自己对于生命的感悟与激情。
凌宇先生的人文主义的学术立场与坚守“文学是人学”的信仰来源于“五四”以来的人文主义思想启蒙运动,来源于新时期拨乱反正的思想解放运动,以及他对于随之而来的西方现代人学思想的借鉴与吸收。他指出:“对中国传统文化——符号的全面反思与叛逆,肇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极大地促进了这种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五四运动的最大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见。于是,对人的自我权利与尊严的诉求,成为‘五四’新文学的中心话题。”⑤凌宇先生身处拨乱反正思想解放运动的历史时期,“五四”新文化运动也给他以精神的洗礼,他同时广泛阅读包括苏联学者伊·谢·科恩的《自我论》、卡西尔的《人论》、弗洛姆的《为自己的人》《逃避自由》等人文主义书籍,形成他自己的独特的人文主义学术立场。哪怕在20世纪形式—结构主义的文学批评形成潮流,甚至一些学派认为文学不过是一种与现实人生毫不相干的“纸上的符号”,不过是一种结构的游戏,凌宇先生却依然坚守“文学是人学”这一信仰而未动摇。
二、在历史文化情境与现实语境中进行学术探寻
凌宇先生在文学研究时,不仅将研究对象放入特定的历史文化情境中去探寻,而且还站立在当下的现实语境中,揭示出研究对象在当下的历史意义及价值,显示出他学术研究的双重视角,形成历史与现实的对话,体现出其研究的较为鲜明的历史性与现实性相结合的特征,这种学术思想在沈从文研究和当代湖南文学湘军的研究上体现得非常明显。
凌宇先生在作沈从文研究时,总是将沈从文的文学创作放进那个具体的历史文化之中进行考察,放在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的对照之中,放在苗族文化与汉族文化的对照之中进行,如果说,他早期还重点从社会学的视角论证沈从文不是“反动作家”的话,那么后来越来越明确将沈从文创作作品放在特定的历史文化情境中进行分析研究,揭示其内在的思想内涵。譬如在分析沈从文创作时,就紧紧抓住沈从文笔下的“都市”与“乡村”这两个世界所呈现的不同的人生情状进行论述,他说:“都市与乡村的不同颜色、声音、气味,‘绅士阶级’与‘抹布阶级’迥异的人生情状,结构成沈从文建造的文学世界的两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