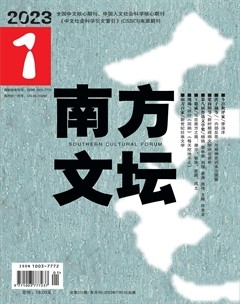文学翻译之盛衰,当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其时的文化之盛衰,一如第八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翻译奖时隔多年后终于评满五部获奖作品,亦可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这个时期的文化之繁盛。这种繁盛从有资格参评的送审译著数量上可略见一斑——达到了八十五部这个近年来的最高值;亦可从送审译著语种上得以体现——共有包括英语、德语、法语、俄语、匈牙利语、波兰语、罗马尼亚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拉丁语、阿拉伯语、波斯语、日语、韩语、西里尔语、越南语在内的十七个语种,这些语种所在国家和地区几乎涵盖了整个世界;还可从俄语、圣卢西亚语、阿拉伯语、英语和日语的这五部获奖译著的文类上加深这个印象——计有长篇小说、诗歌、随笔和传记这四大文类,其原著所在国广泛分布于欧洲、南美洲、非洲和亚洲;当然,我们还可以从获得第八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翻译奖殊荣的五位译者的年龄来佐证这种繁盛——以竺祖慈、薛庆国、陈方、杨铁军等老年、中年译者为主,兼顾许小凡这位三十出头的青年译者,体现出我国文学翻译队伍以老带新、后继有人的可喜局面。
这个可喜局面当然来之不易,甚至可以说是相当不易!在此前七届的评审中,除了第一届和第二届评出五部优秀译著,其后五届都未能评满五部译著。尽管这种现象雄辩地明证了鲁迅文学奖文学翻译奖宁缺毋滥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却也显现出文学翻译界的翻译质量断崖式下跌的尴尬局面。尤其在第五届评审中,竟然连一部优秀译著都未能评出。2010年11月4日的《天津日报》曾对此痛心疾首地叹息道:“文学翻译类作品首度出现空缺,未能评出一部优秀翻译作品,中国翻译界定格在了永远的遗憾,同时也给文学翻译工作敲响了警钟。”之所以出现这种“永远的遗憾”,细究起来大致缘于以下几种困境。
我们首先探讨其中的经济因素。20世纪50年代,由于历史原因,早年曾留学日本的周作人和钱稻孙的生活比较拮据。得知这个情况后,周恩来总理专门指示人民文学出版社以稿酬形式每月向这两人提供生活费用,同时发挥两位先生的专长,让他们自行选择日本古典文学作品进行翻译,完成后将译稿交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即可。当年,这些稿件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并未立即出版,而是堆放在仓库中,直至改革开放之后的20世纪80年代才陆续编辑出版。然而,在利润至上的当下,恐怕在全国再也找不出一家像这样长期只是付出却没有回报的出版社。为了牟取最大利润,翻译稿酬不仅未能随着生活水平的改善而相应提高,一些没有底线的所谓“文化公司”甚至寻找在校外语专业本科生进行翻译,以便将稿酬压至最低水准,同时也将翻译质量折腾得惨不忍睹。客观地说,在当今文学翻译界,如果仅靠翻译稿酬收入是完全无法生存的。当然,这只是出版市场近年以来的乱象。也就是说,这种乱象并非古来有之。众所周知,鲁迅先生的文学活动始于外国文学翻译,他用大半生精力翻译介绍和研究外国文学,共译介了十四个国家约一百位作家的二百多种作品,还曾于1934年创办专门译介外国文学作品的杂志《译文》,在为我国的文学翻译事业作出巨大贡献的同时,其本人也从翻译实践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自不待言,鲁迅先生的生活费用主要也是来自这些文学作品的翻译稿酬。再如我所任职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原所长、俄苏文学专家叶水夫先生曾翻译《青年近卫军》一书,其后用这部篇幅并不很长的译著稿酬在北京买下一座四合院。真是不敢想象,倘若这两位先生仍然健在并生活于当下,他们原本依靠翻译稿酬维持的生活将如何支撑下去?鲁迅先生那三百余万字的译文和叶水夫先生翻译的《青年近卫军》不知是否还会问世?倘若这答案是否定的话,我们民族和国家原本源自于外国文学作品的那部分营养是否会随之缺失?……这种乱象造成的直接恶果,便是在我国彻底消灭了以文学翻译为职业的专业翻译家,原本应由这些早已不存在的专业翻译家产出的大批优秀译著也随之灰飞烟灭,只能转由一些具有文学翻译能力却处处受制(下面将另行讲述)的学者兼职从事这项工作。如何“复活”大批专业翻译家,使其稿酬能够维持家庭必要开支,使其能够心无旁骛地产出大量优秀译著,便是摆在我们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了。
制约文学翻译的另一个困境是学术机制因素。除了经济原因,学界本身的机制也存在很大问题。不知从何时起,外国文学研究机构和诸多大学都有一条成文或不成文的规定,那就是文学翻译不能算作学术成果。毫无疑问,这是一种非常错误的谬论,这种谬论认为文学翻译只是一项简单的文字置换工作,并不需要学术修养,也没有什么学术价值,因而不能算作学术成果。这就使得很多具有翻译能力的学者不敢把时间和精力花费在文学翻译上,因为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翻译出来的译著,一是挣不到像样的稿酬,二是不能算作学术成果,甚至有可能被指责为“不务正业”。最初制定这项规定的人可能并不知道,如果没有相当程度的学术修养和研究能力,是绝对译不出好的译著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