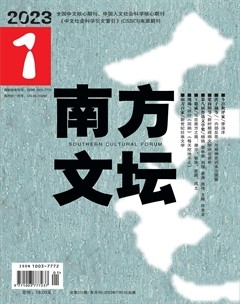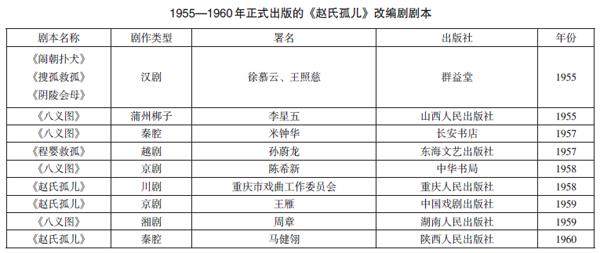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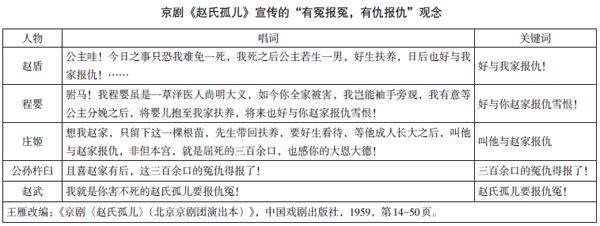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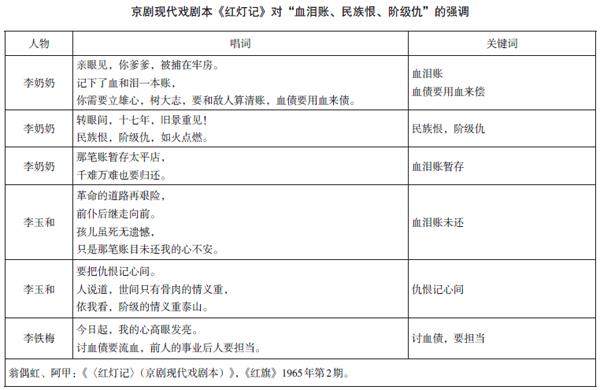
“紅灯记”通常是指被列入“样板戏”的现代京剧《红灯记》(1964),其故事梗概源于沈默君(笔名迟雨)和罗国士(笔名罗静)创作的电影文学剧本《自有后来人》①(1962)。在电影剧本《自有后来人》发表之前,其实出现了多部以“红灯”作为题名的作品,如源自宋元戏文《林招得》的传统剧《红灯记》和收录进“中国人民文艺丛书”的现代越剧《红灯记》,但这些关联剧未能进入研究者的视野。袁成亮《红色经典〈红灯记〉诞生始末》②、谢伯梁《荡漾在电影与戏剧之间——〈红灯记〉系列作品的逻辑演进》③、刘灵《京剧〈红灯记〉的起源》④等代表性研究均未提及上述作品。拙作《“红灯记”的文艺改编史》⑤曾对电影剧本《自有后来人》至现代京剧《红灯记》的文艺改编情况进行梳理,但也未涉及电影剧本《自有后来人》之前的“红灯记”作品。本人指导研究生刘吉丹完成学位论文《“红灯记”创作与改编研究》⑥,限于梳理“样板戏”《红灯记》形成前后的系列作品,也未能从古今演变角度勾勒“样板戏”《红灯记》与此前剧作的关联。
从古今演变角度来看,来源于传统和民间的创作素材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不仅“红灯记”这个具有吸引力的剧作名称源远流长,而且“红灯为记”“痛说家史”这类情节在此前传统剧中就已经存在。旧剧“的笃戏”改造过程形成的现代越剧《红灯记》创作实践已经预示日后沪剧《红灯记》和现代革命京剧《红灯记》为何会产生以及如何产生。
一、民间传奇《红灯记》的深远影响
传统改编剧《红灯记》源远流长,迄今可追溯至宋元公案《林招得三负心》。据戏剧史家钱南扬在《宋元戏文辑佚》考证,虽然《南词叙录·宋元旧篇》篇名《林招得三负心》,但林招得并无负心事,“三负心”系上文《陈叔万三负心》衍生,故《林招得三负心》实为《林招得》。《宋元戏文辑佚》据《林招得孝义歌》录其本事如下:
陈州林百万子招得,与黄氏女玉英指腹为婚。不幸林氏屡遭灾祸,家道中落,招得只得以卖水度日。黄父嫌他贫穷,逼他退婚。玉英知道此事,约招得夜间到花园里来,要以财物相赠。事为萧裴赞所知,冒充招得,先到花园里去,把婢女杀死,抢了财物逃走。黄父就以招得杀人诉官。招得受不起刑罚,只得招认,判决死罪。后来包拯巡按到陈州,辨明招得的冤枉,把他释放。招得入京应试,中了状元,终与玉英团圆。⑦
《林招得》最终演变为跨地域流传的多样化民间文艺样式,如地方戏剧、民间宝卷、传奇小说等。山西大学尚丽新教授指导的硕士学位论文《“红灯记”故事的流传》⑧和其与车锡伦合著的《北方民间宝卷研究》对此有较为详尽的剖析。与本文主题相关的问题是,宋元公案故事《林招得》演变成民间传奇文艺《红灯记》,为何会被赋予“红灯记”这个具有特殊含义的名称?尚丽新和车锡伦合著的《北方民间宝卷研究》认为,不同作品由于口传、手抄、改编等多方面的原因导致了其叙述侧重差异,《林招得》故事流传存在“《卖水记》—《赵美蓉观灯》—《红灯记》”三个阶段发展,对应的是“孙继高卖水”“赵美蓉观灯”“以红灯为记”三种情节。
“红灯记”故事在孙继高卖水和女扮男装救夫两大基本情节的基础上不断地演化。男主人公孙继高这一角色没有大的发挥余地,相对稳定,变化最少,其他人物和情节均处于不断变化之中。总体上来看,这个故事的演变趋势是由简单到复杂,大致经历了从“孙继高卖水”到“赵美蓉观灯”再到“红灯记”三个阶段。最初模仿“卖水”故事,就叫“孙继高卖水”;然后随着赵美蓉观灯的盛行,又出现了《东京》《赵美蓉观灯》这些名称;再到后来随着挂灯的情节越来越精彩,才出现《红灯记》《双灯记》《白灯记》一系列与灯有关的名称。⑨
笔者认为,这个观点确实有一定道理,因为从逻辑上说,只在“以红灯为记”情节出现之后才会出现《红灯记》命名,山东地方戏《赵美蓉观灯》不仅以“灯”作为剧作命名,而且在剧情方面突出“元宵观灯”和“红灯为记”的主要情节。据笔者查证,山东茂腔、柳腔、扽腔、吕剧等均有相应版本的《赵美蓉观灯》,这些剧作仍然继承了《卖水记》中的“悔婚生变”和“沉冤下狱”叙事框架,但叙述侧重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以柳腔《赵美蓉观灯》为例,全剧切换成以女方为中心,甚至全剧都没有男方当事人出场,“沉冤下狱”只是作为叙述背景,“元宵观灯”演变成重要情节,“花灯”发展成极为重要的接头暗号。
今日正是元宵佳节,宝童婶娘言道,借观灯之名,前来与婆母吊孝。要我门前高挑花灯为记。我想趁此机会,多多描上几盏花灯,我叫它五步一棚,十步一盏,悬挂长街,一来为她引路,二来供她鉴赏,也好表表俺的敬意。⑩
这些确实能够证实,新增的“元宵观灯”和“红灯为记”情节直接导致了《红灯记》命名的出现。值得商榷的是,这并不一定证明《赵美蓉观灯》和《红灯记》存在直接改编关系。事实上,清代《绣像说唱红灯记》的第十五回“约赴红灯主仆用计”已经出现了“外出观灯”;第十六回“孝披白服泣哭瞻灵”出现了“以红莲灯为记,为孙母吊孝”情节:
他主仆出城来至东关外,他见了一街两巷黑古咚。莫非是孙家爱姐年纪小?他当紧的别忘了挂红灯。正是这小姐走着心害怕,猛抬头路北闪出红莲灯!他二人大门以外下了马,上前去手拍门扇叫一声。11
清代佚名传奇小说《双灯记》第四回为“赵兰英赠银葬姑,定巧计门挂双灯”也同样出现了类似的“以红莲灯为记,为孙母吊孝”情节:
爱姐说:“这有何难?婶母若去吊孝,去年俺奶奶给我买了一对红莲灯,到十五晚上把这双灯挂在咱那大门上,看见红莲双灯就认的是咱的家了。”12
清代鼓词《绣像红灯记》和佚名传奇小说《双灯记》均出现,女方以“以红莲灯为记”前去吊孝,这些情节也同样能够解释《红灯记》命名的原因。既然如此,从《卖水记》直接发展到《红灯记》,这也不是说完全没有可能。就此而言,“江湖十八本”剧目能够对这个观点提供一定支撑。“江湖十八本”是民间戏班在长期演出过程中逐渐整理出来的经典剧目,其中的剧作既受戏班推崇,又受观众欢迎。
出版过专著《“江湖十八本”研究》的白海英女士认为,“江湖十八本”之所以能长期流传,是因为当时的戏班通过经典剧目而不是名旦演员来留住观众,即“戏保人”而不是“人保戏”13。既然“江湖十八本”是通过经典剧目招徕观众的模式,那么“某某记”三字模式无疑有助于观众熟悉和选择剧目,从这个意义上说,《卖水记》更名为《红灯记》,未必就一定经过《赵美蓉观灯》这个环节。除此之外,“江湖十八本”同剧的异名现象也是值得注意的。或为押韵,读起来朗朗上口;或为易记,令人过目不忘;或为强调,突出精彩情节;不同戏班的相同剧目出现不同的命名。从《卖水记》到《红灯记》这样的调整,似乎更加令人过目不忘,而且也突出了精彩情节。考虑“江湖十八本”的时间,始于元明,熟于明清,再结合“江湖十八本”被戏班当成标榜实力、吸引观众的招牌,我们完全有理由推断:《卖水记》《红灯记》《双灯记》《白灯记》都有可能以“同剧异名”的方式列入某些戏班的“江湖十八本”。至此我们可以这样说,宋元公案《林招得》《红灯记》的形成确实存在着一条从宋元公案《林招得》、明代南戏《卖水记》、清代鼓词《绣像红灯记》这样一条发展路线图。这并不是说上述作品构成了直系亲属般的继承关系,毕竟同一时期存在大量同名或异名的民间异作,其实很难证实为数众多同名和异名作品之间的演进关系,但即便如此,作为不同时代的代表作之一,这些作品已经能够清晰揭示出不同时代作品的演进关系。
从剧作内容角度来看,“样板戏”《红灯记》与此前的民间传奇《红灯记》的关联确实是有限的,主要是限于双方以“红灯”作为接头标记,但从剧作借名角度来看,民间传奇《红灯记》作为经典剧目,广泛而长期流传带来的社会文化影响则不言而喻的,像《红灯记》《白灯记》《双灯记》等入选“江湖十八本”就是很好的证明。如果我们将“江湖十八本”看成是不同剧组推出的“拳头”产品,或者将“江湖十八本”看成是剧组推出的“招牌”盛宴,那么日后同名的《紅灯记》剧作又怎么不可以看成是文艺创作领域出现的“傍名牌”。在互联网时代,我们看到为数众多的互联网公司花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用于流量建设,究其原因是希望自己的公司和产品获得更多的关注,毕竟人们花费在互联网上的时间和注意力都是有限的,所以出现了“蹭热点”和“蹭流量”的现象。在农耕文明时代,人们对文化娱乐的关注也是有限的,如何将人们极为有限的关注转移到自己的剧作上来,这恐怕是编剧和演员共同感兴趣的话题。传统旧剧广泛流传且经久不衰已经产生了类似于“品牌”的流量效应,推出传统旧剧同名作也可以看成是农耕文明时代的“蹭热点”和“蹭流量”,而这样做所带的“传播速度快”和“爆发效果猛”恰好符合革命功利主义文艺创作的要求。
对《红灯记》创作改编的“借名”现象,我们应该从“社会主义文艺生产”的角度来看待。“文艺生产”主要是指作家是应当时政治和政策的需要进行创作,而“社会主义”提倡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则意味着创作题材、作品名称、故事情节、人物形象等都可以成为直接调用的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