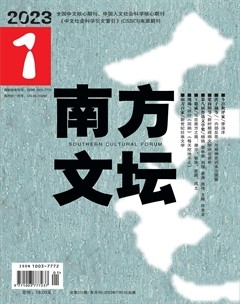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观念转型以及90年代文学桂军的“边缘崛起”,新世纪的广西文学呈现出多民族文学多元共生、文体丰富的新局面①。其中,壮族作家的散文创作也在时代的潮流中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新态势。从创作队伍来说,新世纪以来从事散文创作的壮族作家梯队整齐、力量壮大。生于1930年代的韦其麟、凌渡依然在坚持笔耕,生于1950年代的冯艺、庞俭克、黄佩华、岑献青和生于1960年代的严风华、石一宁、凡一平、牙韩彰、黄鹏、黄少崇、蒙飞、透透等作家还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力,生于1970年代的陶立群、罗南、黄土路、梁志玲、韦露、廖献红等作家的散文开始走向成熟,生于1980年代的黄庆谋、黄其龙和生于1990年代的廖莲婷等新生力量也显示出良好的创作势头。从作品数量来说,几代作家携手共进,持续发表新作,同时推出了大量的散文集。在1999年出版的《百年广西多民族文学大系·散文卷》中,共收录新世纪以来的散文56篇,其中壮族作家的散文13篇,接近四分之一。从创作特质来说,新世纪以来的壮族散文延续了壮族作家自觉的民族意识,立足民族土壤,拥抱民族文化。同时,也具有开阔的胸怀和开放的视野。2007年,壮族散文家冯艺在《根性的写作》中提到,民族文学的“根性”来源于自己民族的文脉,“真正的少数民族作家,他的笔下,永远流淌着母体的血脉和浓浓的原乡况味”,“这是一种根性的写作,他们的根扎在民族母体里”②。从本质上说,新世纪以来的壮族散文创作正是一种“根性写作”。民族根性是深潜于少数民族作家意识中的身份认同与民族自觉,是一种可勾连历史记忆与写作主体的文化质素,也是理性反思下回望民族与自我的某种诗性思考。在全球化、城市化、多样化等特征显著的新世纪,民族之“根”更需要扎根在特定时代的文化土壤之中,立足当下,以一种发现、发展和审视的眼光拥抱现在和未来。正如冯艺所说,民族文学的妙谛是“民族根性和与时俱进的大胸怀交融糅合”③。新世纪的壮族文学在中国多民族文学繁荣共生的背景下,正以一种自觉扎根民族母体、竭力重续民族血脉、积极拥抱现代文明的与时俱进的姿态和“大胸怀”持續在文坛深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相比于小说,壮族散文以某种“真实”的倾向和抒情的方式试图抵达民族的根脉,对山海文化性格与民族历史记忆、“那”文化浸润下的土地意识和“麽”文化陶染下的万物有灵等民族历史、伦理和文化质素进行理性的审思与诗性的思考,发掘了壮族散文与一座山、一条河、一棵树或一朵花坦荡于穹庐间的同脉共生的民族气质。这种立足民族传统,观照历史、文化与生命的“根性写作”,显示了新世纪壮族作家深入多彩地域和民族根性中汲取创作养分的文化自觉。
一、山海文化性格与民族历史记忆
八桂多山多水,山河相间,居于其中的壮族常被冠以“山地民族”的称谓。事实上,广西不仅处于珠江水系中的西江流域,桂东南与广东珠江文化一衣带水,桂南还有海岸线和边境线,也可以说是一种准海洋文化。正如严风华在专门介绍广西世居民族的散文集《壮行天下》中提到:“一片土地,如同身躯;一片海洋,如同血液。身躯有了血液,才会变得鲜活,脸色才会红润。广西有山有海,山海相连。从山到海都是壮族的家园。也就是说,壮族拥有了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拥有了丰富的山地资源和海洋资源。更重要的是,拥有了海洋一样的博大、宽容、开放、开拓的性格。这是我们壮族生存的根本。”④正是千百年来与山峦海河的共处,壮族人民不仅获得了刚毅、坚韧、宽容的山地秉性,也拥有了开放、拓展、进取的海洋性格。这种性格在民族融合、多元共生的新世纪背景下赋予了文学创作以一种面向历史、奔赴未来、海纳百川的“根性”。
这种“根性”集中体现在广西当代小说和历史文化散文之中。与小说创造诡谲多变的异度空间不同,新世纪壮族作家的历史文化类散文立于山海民俗的现实空间里抒情达意,思绪纵横古今中外,如江河湖海般气魄宏大,同时重视历史遗忘的焦虑和危险,在故事和传说中捕捉即将逝去的一些细微的、可能的真实,以抵抗记忆的程式化消散和无根的现实隐痛。牙韩彰散文集《屈指家山》中的“八桂文化名山寻访系列”和“回望家山系列”散文以真挚的感情、淳朴的笔触和趣味的意兴将珍藏在故乡和心中的山、景与历史捧在读者面前,并道出了他的忧虑:“一个没出过名人的家族或村庄,最后的结局,必然是默默失语于时间的长河而无声无息,外人既不知其来路,更不知它将要走向怎样的未来。”⑤诗人黄鹏的散文集《气象家园》用强烈的情感守护以花山骆越文化为根脉的民族文明,反思当下商业浪潮对民俗文化和风土人情的侵蚀。他呼吁关注本民族失落、寂寞的文化:“与其热衷于仿古建造,与其崇媚他地他国的文化文明,不如回过头来关注我们寂寞的文化文明,不如认真审视一下我们是如何对待自己的历史文化文明的。我们应该相信,神州大地上人和一个民族创造的文化文明,其价值绝不会低于其他地方的古迹,都是值得全民族共同守护、视如明珠的。”⑥蒙飞的《花山蝴蝶飞》以虔诚的心态回顾花山的历史文化,寻找壮族的精神家园:“我已是多次前来拜谒花山了,带着一个壮族赤子的虔诚之心。每次前来,心灵都获得一次洗礼和升华。在民族坦荡赤裸的图腾面前,我感受到来自心底的震撼。感觉到自己的灵魂在颤抖,在燃烧。随着拜谒次数的增多,我一次比一次坚信,呈现在我面前的赭红色花山壁画,就是壮族先人热血澎湃的心脏,就是壮族先人的心血之作。”⑦历史文化类散文的持续繁荣展示了民族作家以历史为根基、以本民族文化为根柢、以个体认知为依托的“与时俱进的大胸怀”。
冯艺的散文集《红土黑衣——一个壮族人的家乡行走》《沿着河走》《除了山水还有什么》在文化历史题材的书写中时常感叹历史余痕逝去的悲哀,袒露历史记忆遗忘的焦虑。在《红土黑衣——一个壮族人的家乡行走》中,冯艺将壮族民族风情和故事融入一幅巨大的历史素描中,把吊脚楼、山歌、花山崖壁画、壮锦、绣球、三月三、天琴、红水河等壮族标志和苏元春、陆荣廷、孙中山、莫氏土司、张天宗、瓦氏夫人等历史人物悉数数来,以发现的眼光、行走的姿态构建了历史记忆中的现代民族风景,守护文化根脉的同时不断提醒失去历史记忆和反思意识的危险。冯艺感叹道,失去历史深刻性的人们“普遍缺乏记忆的真髓、血性与骨质,缺乏知觉、沉痛和耻辱感,更缺乏灵魂的拷问,矫饰、轻浅、单薄、圆滑,不仅不能解释已经发生的历史,而且造成历史真相的模糊、残缺、流失甚至是常识性颠覆”⑧。冯艺的历史文化散文不断确认直面历史的重要性,重申历史记忆对民族文学的“根性”塑造,具有一种史诗般的气魄。瓦尔特·本雅明认为,“历史地描绘过去并不意味着‘按它本来的样子’(兰克)去认识它,而是意味着捕获一种记忆,意味着当记忆在危险的关头闪现出来时将其把握”⑨。冯艺的散文不拘于对历史事件本身的认识,试图捕获一种历史主体的记忆并用于还原多维视角的真实,这是一种开放的、进取的、直面历史与现实的文化态度。历史与记忆在冯艺的散文相伴而生、相辅相成,记忆则具有了通向过去、未来和自我的可能。《沿着河走》和《母亲记》都将家族记忆与浩荡的历史相勾连,试图在历史的总体性中发掘某些幽暗的悲哀。在冯艺的散文中,个体的记忆和历史是同脉共生的,人就是历史本身,个体的经验世界深深地扎根在历史长河之中。冯艺散文正立足于现实的“当下性”,沿着经验世界的长河奔向想象世界的海洋,探寻一种保留复杂性和反思性的整体性书写。在遗忘的焦虑和记忆的寻真之外,冯艺的散文还具备一种积极发掘和建构中华民族精神的“大胸怀”。在《古老运河的娃娃们》中,冯艺在苏北运河边想起了抗战时期由一群娃娃组成的“新安旅行团”。娃娃们一路南下,以多种艺术形式组织青少年,动员民众,宣传抗日救亡,在桂林文化城中留下了多篇剧作,也在南宁昆仑关血战前线为将士们演出,他们“用脚步度量着生命的意义,也在社会中学习成长”。冯艺感叹道:“少年的前途是浩荡无涯的,少年的锤炼也是不可限量的,中国的未来,不正是靠着这样一代代古老运河的娃娃们吗?”⑩这种“向上,向大千世界,向远方”的力量,正是民族的未来,中国的未来,是值得被铭记和发扬的中华民族精神。
在山河湖海和历史记忆中穿行的还有石一宁、严风华、黄佩华、黄土路等。石一宁关于履痕心绪和寄情哲思的《凌云行思》《北海的风》《上林忆想》等散文以强烈、自觉的民族主体意识介入历史记忆,呈现出一种心怀天下、品味历史、拥抱现实的广阔风貌。严风华散文集《壮行天下》《龙州记忆》《总角流年》,黄佩华散文集《生在平用》,黄土路散文集《谁都不出声》等,都有不少篇章着力书写壮乡的风土地貌、历史余痕和个体与历史的同脉共生,在不放弃历史总体性的态度之上,将强烈的主体嵌入时代的轨道,追求一种更具有“汇通性”的整体性。沿着文化寻根的脉络和视角,新世纪壮族散文用山海一般宽广的视野立足现实,用强烈的主体意识挖掘历史断裂中的真实,虽然在历史地标和故事的选择上略有重复,但仍切合了新世纪文化的总体要求,对广西文学的文化根脉进行了再次确认,也重塑了新世纪民族文学情感的重量和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