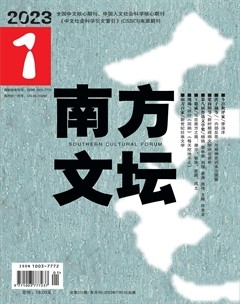21世纪是一个科技高速发展的世纪。这个新世纪在已经展开的头二十二个年头里,人们完全沉浸在科技发展带来的更加丰富、便捷和舒适的生活中,与此同时,从人与人、人与社会到人与自然的关系等无数层面,许多革命性的变化都在悄无声息地进行着。现实世界以及通过网络投射的万花筒一样的世界已经让人眼花缭乱,可以说,这不是一个能够让人静静阅读的时代,不是一个文学的时代,更不是一个诗歌的时代。但也正是在这个看起来不合宜的时代,文学欣欣向荣,诗歌蓬勃葱郁,都在努力捕捉、洞穿这个万花筒一样的世界,努力在排山倒海的新媒体攻势、铺天盖地的网络信息世界中占有一席之地。张清华在回顾新世纪以来的诗歌发展史的时候,感叹“没有哪个时期的诗歌能够像这个十几年这样,是如此自在和内部地发生发育着,争执和分化着,裂变和成熟着”。他用“疯长”①来形容这一时期的整体诗歌概况。
相对于广西当代小说在文坛以品牌化方式的集体亮相给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广西当代诗歌稍显寂寞。但新世纪以来广西诗歌整体上同样呈现出一派繁荣热闹的景象。而其中,在广西少数民族诗人队伍中,壮族诗人是绝对亮眼的一支。
首先从诗人队伍上来看,可以说是“四代同堂”:50后、60后壮族诗人冯艺、石才夫、大朵、韦佐、黄鹏等;70后壮族诗人黄土路、黄芳、荣斌、许雪萍、韦漢权、蓝向前等;80后壮族诗人牛依河、艾芥、费城、覃才、划痕、微克等;90后壮族诗人粟世贝、黄钰晴、廖莲婷等,还有上海的崖丽娟等都不断有诗作在各地刊物上发表。其次,新世纪以来,壮族诗人相继推出自己的诗集②。这些诗集既是诗人一个时期创作的总结,同时也是“壮人”当下精神图景的集体展示。2013年广西文联、作协推出十卷本“广西少数民族新锐作家丛书”,其中只有两本诗集,分别是壮族诗人费城的《往事书》和黄芳的《仿佛疼痛》。最后,在广西活跃的民间诗群中,有不少壮族诗人。如荣斌、费城、牛依河是2013年12月成立的西乡塘诗群主要成员,后二者还是南楼丹霞诗群的主要成员,大朵是2010年创立的麻雀诗群的主要成员之一。
回顾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叙事,从“他者阐释”到“主体阐释”,从“共名叙事”“正名叙事”到“匿名叙事”③,以及“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和解”“地方与全球/民族与世界”“封闭的神话的重述历史”④等,这些从不同层面上的诠释和归纳,同样是理解当下民族文学写作不可缺少的框架。新世纪以来的壮族诗歌,从以韦其麟、莎红、侬易天为代表的第一代壮族诗人的民族叙事,冯艺、黄神彪、黄堃等为代表的第二代壮族诗人的“花山书写”,牛依河、费城、覃才等为代表的第三代壮族诗人的“壮人书写”⑤,在时代的快速变化中,呈现出更多复杂的特征。诗人们不仅要面对新诗传统、地方性写作问题,同时要面对世界写作,进行地方经验、全球视野、民族身份、多元文化等的深度融合。在这个意义上,这里尝试从“民族性的彰显与超越”“双重异乡人”“模糊的认同与景观化”三个层面来描述几代“壮人”当下的大致精神图景。
一、民族性的彰显与超越
对大多数有理想的知识分子而言,诗言志传统无疑深入骨髓。一部当代诗歌史,同时也是个体与国家现代化建设同步成长的精神史。作为深受20世纪上半叶革命传统的影响,亲身经历了后半叶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艰难历程,见证了国家的崛起和复兴的诗人,20世纪50—60年代出生的壮族诗人,尤其是深深卷入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曲折发展过程的个体,他们的诗歌写作也因此格外引人深思。壮族诗人冯艺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冯强认为冯艺的诗歌呈现出融合国身通一的红色革命传统、天人合一的古典自然传统以及新文化革命传统三大诗歌传统的复杂灵魂状态⑥。的确,冯艺的诗歌写作与其散文写作相辅相成,既有自觉的民族身份认同与民族历史文化寻根的民族性书写,又有超越民族性的传统叙事主题的延展,个体与历史的和解,以及对生命的叩问。换句话说,在冯艺这里,家国、民族、自我与天地融合一体无间,在他的笔下依然洋溢着大我的豪情,颂赞的是社会原子化之前的人间大爱,诗歌的情感基调是明亮的,是对美好理想的追求和引领。
冯艺以从容的壮乡大地、世界各地的行走串起一颗颗情感的珍珠,以诗歌的方式接续历史的文脉,拨开尘烟掩埋的历史形象,用个人化的书写唤起早已消逝的激情燃烧,也在行走和书写中重塑理想自我。那大开大合的情感手笔,目光如炬,从历史迷雾中穿尘而出,叩击欲望都市里精神贫瘠的现代人:“思想的灯/在黑暗里努力发光”(《绚烂收场——写给唐景崧》),“本来忠肝义胆 智勇双全/步履如此铿锵”“比水晶还清澈的眼睛”(《忠诚——写给袁崇焕》),“遇见一位大儒/炯炯有神的目光/坚定 纯洁/刚正 智明”(《临桂四塘乡》);看到边缘崛起的步履蹒跚:“你用边地人的/目光/拉近蛮边/与中原的距离”(《读张鸣凤》);看到老乡“从早起的黎明/到晚归的黄昏”(《老乡》)的“创作”,和自己无法不回头的十万大山。思考“中国向何处去”,也叩问“人活着为了什么”(《最后的儒家》)。他在诗歌中与历史和解,四十多年前的那一场“辽远而刀削的风”,那一阵“凶猛而恐怖的火”(《克拉玛依的风与火》)在生命中划出一道深深的印痕,但如今“我知道自己已在风中悄然老去/我只会用平缓的呼吸/把故事逐一向自己再讲述一遍/再把它写在取走的这张桦树皮上 铭记”(《今夜我在阿勒泰》),“把紫色的痛苦/藏进抽屉/但不要冷却/温馨的希冀”(《不要把昨天都忘记》)。他在遇见的万物中释放自己敏感的天性,与自己展开生命的对话。“我无法/把一片片落叶/喊回树上/就像我/无法把/自己的影子/喊回我的身体”(《看见落叶》),生命的原色是“时常保持/简单而朴素的愿望/就能看到/后面的坚韧”(《旧物》),身心沐浴在自然山水中,洗练出一个更加澄澈坚定的自我,“我庆幸今日进入/一条冰冷的溪流/把许多念想/冷藏在水里”(《冷冻》),“我对美好的山水/心存感激/我对善良的人们/无限敬意”(《山歌好比春江水》)。
如果说在冯艺这里,壮族的根性特征已经与更博大的文化融为一体,呈现出开放的现代人风貌,大朵的诗中则还有一股没有被现代文明磨灭的原始力量,在面对神秘的花山岩画时喷薄而出:“唯有敬仰才能打开灵光/唯有沉默才能让血脉对接/祖先密码……仰望这高高的崖壁/阅读一部不朽的民族史/一股雄性的力量/灌满我身心”(《仰望花山》),这是一股来自壮族祖先的绵延不息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