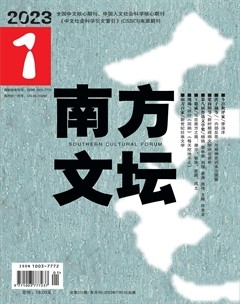这里的南方不是指作为江南的南方,而是五岭之南的大部分岭南地区,包括广西、广东、福建、台湾、云南、贵州、海南甚至东南亚等地。这一地区自古就远离中原和江南文化区,有着原始、野性、开放、融合的文化特征和临海、临边的地理特征。在这个区域聚集着苗、瑶、侗、壮、黎、彝、回、汉等众多的民族,形成多民族融合的文化多样性。从汉代开始的海上丝绸之路、明朝的郑和下西洋到近代开放的通商口岸,再到改革开放的最前沿,这个区域一直都是以开放的姿态面向世界的。该地区地处陆地和海洋的临界处,是多国边界交汇的地方,多元的文化环境缔造了包容、开放的文化氛围,新南方影像在这样的文化影响下应运而生。
新南方影像的创作强调南方的文化主体性,具有边缘、野性和融合的特征,这种“新”体现在对影像观念的认知上,体现在对自身地域属性的超越,体现在面向世界的眼光和世界性的认知。艺术家们大多在这个区域生活和创作,也有一些以南方生活为创作题材的艺术家。他们中的大多数出生在1970、1980年前后,也有一部分60后和90后,作品主要包括在南方这一区域拍摄的静态影像(照片)和动态影像(纪录片、实验片、剧情片)。他们的作品通常处在一种旁观的角度,不介入、不干涉,让被摄对象自在地表现,这种边缘与旁观也体现了创作的自由;“野性”不但体现题材内容的山野原始,也同时体现在对规矩的打破。这样的创作理念在阿彼察邦的《波米叔叔的前世今生》、蔡明亮的《爱情万岁》、王兵的《三姊妹》、曹斐的《谁的乌托邦》、朱岚清的《负向的旅程》、程新皓的《莽》、郑毅的《唱山歌》、刘宪标的《春天会回来》等影像作品展中得以体现。
一
新南方影像的第一个特征是边缘性。这里所说的南方,在文化层面上,与北方兴盛已久的中原文化、江南文化相比,显得边缘,但边缘并不意味着被边缘化。台湾导演侯孝贤在《煮海时光:侯孝贤的光影记忆》里谈到边缘时这样说道:“人在中心看不到自己,在边缘才看得到。”①边缘意味着一种旁观的视角,一种冷静的观察,也带有一份远离中心的自由,而这也成为南方这片土地上的艺术家们的一种创作优势。导演王兵在云南拍摄纪录片《三姊妹》时,采用的是冷静客观的旁观视角,不介入被拍摄者的态度,只是用摄影机连续不断地观察。在拍摄时强调开机就拍完一盒带子的方式跟拍被拍摄者,连续的跟拍镜头形成了一段段60分钟的真實时空,他用这种连续跟随的拍摄方式让被拍摄者在镜头前摆脱表演和不自然,也让摄影者投入到被拍摄者的语境中,达到一种人机合一的摄影境界。台湾导演蔡明亮在拍摄《爱情万岁》时,使用较多长镜头进行拍摄,摄影机与观众都处于一种旁观者的视角,持续不断地观察着身处在冰冷的高楼大厦内人的生活变化,将人在现代化、城市化中走向异化的状态展现得淋漓尽致。菲律宾导演拉夫·达兹的影像表达中,边缘感更为突出,在其2014年的作品《今来古往》中,拍摄对象中有一对老人,他们在谈话时突遭洪水,情况危急。然而,直到他们被水完全围困,镜头也没有挪移半分,依然在一旁冷静地注视着他们,异常客观地表现着面对洪水这一南方常见自然灾害的真实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