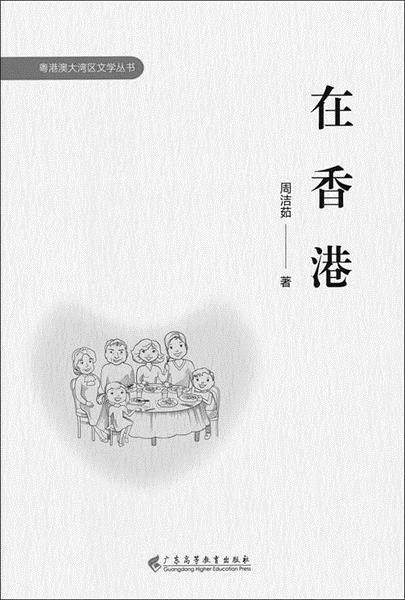
从20世纪90年代出道至今,周洁茹的作品给人一种强烈的空间感。尤其是她的城市小说,地理概念一直是最重要的部分,这似乎与她本人的旅居轨迹相关。据此,我们可绘就一幅文学创作地理图,以见证她从成名、离开到最后回归的游牧之旅。接近十年的美国经历,也使她的作品多了一层世界意识。一直流浪与漂泊,艰难地寻找存在的意义,最后将香港作为回归落脚点,也是她以“他者化”视角来观察世界的选择,以解域化思维和跨界身份对人性做深入地挖掘和思考。而支撑她走过一段又一段的人生旅程,便是爱。2015年是她正式“回归”文坛写作之年,开启了“新移民”系列,在重新认识世界的过程中,她也逐渐对香港产生认同感。香港在她生活第八个年头后正式成为心中的“这里”,对香港的融入使得她的写作精神和文本审美呈现出不少“新南方写作”的特质。2019年出版的散文集《在香港》,从一个“在”字可读出她本人对漫游者身份的确认,也可看出她重新出发的渴望,让我们见证这位当年的“美女作家”已转型成为“新南方作家”。
一、周洁茹与“新南方写作”的缘起
周洁茹出生在常州,位处江南地区。古时的“南方”基本指的就是江南一带,因江南长期处于文坛中心。在世界性的视野中,“南方”呈现的是复数性和混杂性特征,比较著名的例子是美国的南方作家流派以及拉丁美洲文学爆炸现象等。近几年,国内各种期刊相继推出“新南方写作”评论专辑。“新南方写作”逐渐变成一个自觉的学术概念,杨庆祥《新南方写作:主体、版图与汉语书写的主权》一文从主体、版图与汉语书写的主权三个方面对这一概念做了定位和理论上的阐释。杨庆祥将“新南方写作”的地理范围定为“南方以南”,也就是:中国的广东、广西、海南、福建、香港、澳门、台湾等地区以及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等东南亚国家①。无独有偶,周洁茹搬回离父母(或家乡常州)距离更近的香港,情感上希望“近一点点”。至于为什么选择香港?在一次访谈中,她是这样提到的:“我停留在香港,大概也是因为香港最后还保留了一些传统的美好的东西,而且香港一直在很努力地保护着这些东西。香港作家们的架构可能都是松散的,因为没有一个人混来混去,大家都要谋自己的生,以写作之外的方式。写作成为真正干净的一件事情。”②周洁茹用“停留”二字,实际上说明她对融入并没有很刻意,只是用一种“旅行者”的眼光来观察这个世界,哪里觉得适合了就选择哪里,比较在意的还是拓展自己、自由写作并回归自己的内心。与此同时,环境对于她来说也不是特别重要,她曾用“流动的风”来形容自己与环境的关系③。刚开始,香港于她而言只是过渡之处,是她人生历程中的“中转站”,没想到停留了将尽八年后,香港正式成为“这里”,也是她承认已“在”的地理坐标。
周洁茹曾写过系列以“到……去”为题名的小说。表面上给人作为漫游者的周洁茹在确认方向乃至追求“寻找”本身的印象,但实际上聚焦的是在路上“来回”的没有安全感本身。没有去的地方而要“去”,不谈“在”某个地方,因为一旦“在”,作家的在地感会很强烈。但周洁茹很少用“在”,从而提醒她需要改换生活地方之时,她的方向往何处前行,最终到达何处。在她的小说中,最重要的就是写与父母关系的小说。她没有办法陪伴在父母身边,所以与父辈间形成了很大的“距离”。而这个“距离”,只能通过作品拉近。比如《到深圳去》,让我们看到作为孩子的“我”,为了给父母寄行李,历经多重困窘艰辛,终于顺利过关到深圳,最后发出“好了!这不要紧了”④的释怀,让读者的心头大石放下,爱的力量油然而生。故乡对于周洁茹而言,是回不去的“家”,可她已下定决心,“一定要活下去,直到回到故乡”⑤,这也是她永远要“去”的方向和目的地。
正因为周洁茹在写作中不会过多考虑自己與周围人和环境的关联,所以她的写作不会有太多的束缚,语言随着感觉和心灵一同呈现,没有太多的刻意雕琢,或为了谁而写作。虽然周洁茹的内心有向着父母的“北望”情结,但她的写作却不会“北望”,而是诚实的“向南方”,也就是立足当下生活的现实和人性的变化,回归自己真诚的内心,表现出一种叙事主体和叙事精神的独立,从而以自身写作的独特性来影响香港文学乃至中国文学的发展。她曾经说过:“如果我写的什么也能够让你哭,肯定是因为我不在高处也不在故意的低处,任何一个站在旁边的位置,我在里面,我写我们,我不写你们。如果我要写你们,我会告诉你。尊重他人的生存方式才能够得到你自己的尊重。诚实是写作的基本条件,如今都很少见了。”⑥诚实地面对写作与人生,是她的“新南方写作”的重要方向。
曾经大红大紫的周洁茹,看到“繁华将要落尽”的写作事业,便毅然决定离开中国,去一个能让她做出“不能写”理由的美国展开生活。十多年后,当她回来重新写作时,她已不再执着于“转身时的华丽”,而是用实际行动面对某些质疑的声音,即作品语言的过时。这种质疑使周洁茹非常愤怒,亦使她认识到回来写作的艰难,并持续思考如何才能更好地写下去。这种内心的叩问给了她前行的勇气和力量,鼓励自己“不过是多一倍的努力,我还活着,就接得回来”⑦。另一方面,支持她前行的理由,肯定是爱,来自父母的期许和爱,她十分同意齐邦媛对故乡的看法,因为“唯一还会爱我,对我有期许的,当然是父母”⑧。在香港的生活,也让她产生书写香港的想法,尽管她坚持的只是在香港写小说,而不是写香港小说,写作的方向仍然朝向故乡。至于写作的状态,她是期盼能“独立写作,内心自由”⑨,因自己是一个不属于地球的“飞来飞去”的流浪者。这种流浪游牧的精神属性正如评论者马兵所言,是与香港这座城市相洽的,而每篇标识出地名的小说,则显现出“她对空间的敏感和对空间所表征的政治文化身份的多重指涉意义的敏感”⑩。在她的心里,即使未能完全融入香港,也仍然不妨碍读者对她笔下“香港”的理解,即颓废色彩浓重的人间风情之地11。无论书写哪个地域的小说,都离不开对“人”的书写,不会因香港的地方性差异所在而忽略了对普遍性意义的理解。周洁茹的创作谈《在香港写小说》已显现出世界性的视野:“我写了香港人的生活状态。就冷漠到残忍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说,这一点确实也是没有地域的界限的。所以对于我来说,香港人也是人,香港小说,其实也就是人的小说。”12实际上,周洁茹对大城市没有太多好感,在她的印象中只有生活过的小城常州是最亲切可爱的,但随着逐步融入香港生活,她意识到不管承认不承认,自己真的是“在”里面了。既然已“在”香港,总得还是要活下去,这促使周洁茹重新思考写作和生活,并将这些思考形成散文集《在香港》。
二、《在香港》与“在香港”写作
周洁茹作品众多,但在内心里,有一个信念始终支撑她前行,那就是:生活永远比写作重要13。因此,无论读她的小说还是散文,都会感受到发自她扎根生活后流露的“真情实感”。这种被评论者蔡益怀高度评价的“锐气和灵敏的触觉”14,使她碰触到生活的细节,进而书写这座城市的“华丽与苍凉”。这种书写生活的真情实感同样表达在新近散文集《在香港》。
《在香港》涵盖了四个专辑,分别是故乡、香港、写作、问答。收录在内的文章的时间跨度超过二十年,其中后两辑把写作和访谈的时间均标识出来,内容先后触及父母亲情、香港生活、创作谈以及访谈录等,可谓是周洁茹从出道至今思考人生和写作的时空集大成者。书名“在香港”给人颇有意味之感,初读题目以为全书贯穿的是周洁茹书写香港的内容,实际上是周洁茹在香港书写并思考人生,同时投射了她的“香港视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