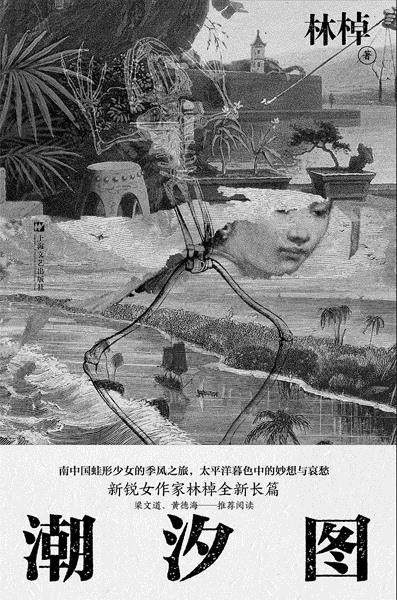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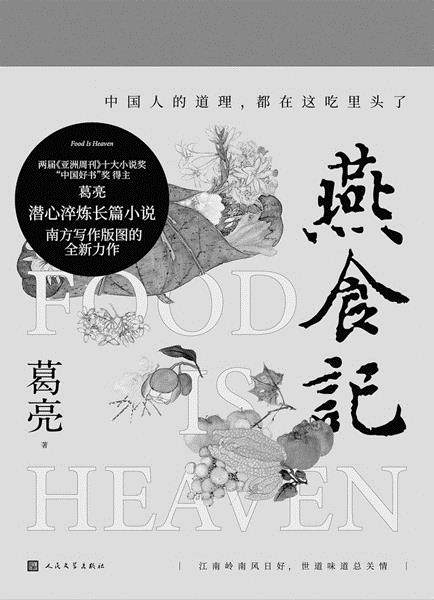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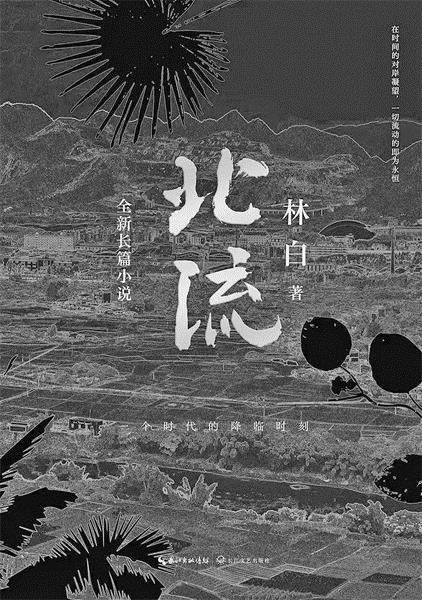
一个地域,无论大小,如果只是自然意义上的,我们对之奉上的赞美就都是属于造物的。同样,如果我们观察的是该地域经济等情形的发展变化,那夸奖就是属于社会文化的。只有当相关作品创造出了特殊的文学形象,所有的讨论和评价才真正是属于文学的。
近年兴起的“新南方写作”,让人们在对该自然和社会的关注之外,自觉地认知属于这一地域的写作特点。虽然关于“新南方”的界定还没有公论,但相对来说,“新南方”的“新”是对于江南地区(旧南方)的“旧”,指涉的主要是广东、广西、海南和福建这部分区域。扩展一点,还包括我国香港、澳門、台湾地区以及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等的华文写作。
概括一个如此广大区域的总体文学状况,非我力所能及。我甚至有时候觉得,与其描述一个庞大而特征各异的群体,不如就从几部具体的作品出发,看看这些作品提供了什么特殊的文学形象和文学思考。出于这个考虑,这篇文章中,要谈论的是与广义粤语区有关的三部长篇——林棹的《潮汐图》、葛亮的《燕食记》和林白的《北流》。
一
林棹《潮汐图》的献词,是一句粤谚,“听古勿驳古”。这真是听故事的好态度。当决定进入一个作品的时候,在接受了起始的虚构契约之后,我们便充满希望,期待作者给出一个合理、精确、完备,受制于自洽(self-consistent)要求的完整世界。在这个自洽的世界里,作者给出的细节越丰富,逻辑越严密,给人的阅读感受就越真实。与此同时,只有遵守这份虚构契约,读者也才能做好准备,接受小说中驰骋的想象。
也果然是奇妙的想象,《潮汐图》从开始就呈现出典型的幻想色彩。作品的叙述者,是一只雌性巨蛙:“我是虚构之物。我不讲人物,因为我根本不是人。我有过许多名字,它们一一离我而去,足以凑成我的另一条尾巴。我会说水上话、省城话和比皮钦英文好得多的英文。一点澳门土话。对福建话、葡萄牙话、荷兰话有一定认识。认得十几个字。”①小说开头的这段自我介绍,包括它的形态、语言、意识,都有明确的设定,几乎给出了叙述功能所需的全部条件。此后全书的叙事,很少有超出或违背这设定的地方,因此,我们可以充分信任这个不会任意变换的叙述主体。
或许正因为这个信任,阅读过程中,我们既想尽快知道巨蛙的命运走向,又舍不得放弃书中的每一个细节。巨蛙的命运和诸多的细节,共同构成了这个作品奇幻而鲜活的特征。也因为这幻想的特征,《潮汐图》得以放开手脚,充分想象1820年代至鸦片战争前夕广州、澳门及与之相连的河海的形形色色,以及徘徊其中熙熙攘攘的各类人物。从这些纵横交织的故事和人物里,我们看到了一个丰富多彩的南方——有根植于这块土地的神奇景象,有富庶繁华的商业往来,也有水上人家的艰苦度日。这一切通过巨蛙的眼睛,又增加了诸多奇妙的部分,再加上把众多原型复合在一个人身上的人物选择,就此展示出这一地域特殊的自然风貌和社会特征。
《潮汐图》的如上特点算得上明显,而更隐蔽但可能更重要的,是作品选择的叙事时间段。在一次访谈中,林棹提到“憩潮期”——“在大概十分钟的时间里,整个海面一动不动,水不涨也不退,也没有风,大海好像呆住了。”小说写到的1820年到鸦片战争这段时间,正是中国近代历史的“憩潮期”:“如果不知道时间,不去看阳光,不去看水位,只是看到那个海面,我们很难预判海水将涨还是退,到底接下来会怎样。这样一个很微妙的时间比较打动我,也符合19世纪末鸦片战争来临之前那个历史阶段的感觉:一切即将发生变化。”②无论对哪个地域来说,这都是一个特殊的时段。传统时代巨大的惯性受到了外来新思潮和新事物的冲击,在特定的时间内似乎势均力敌,岿然对峙,仿佛一切都静止了,但暗潮一直在涌动,更大的事件早已在酝酿之中。
对鸦片战争之前的很长时间段落,最常见的描述是闭关锁国,与外界的沟通几乎断绝。真实的情形,仿佛并不如此,“中国是贫银国,但中国从明英宗正统元年,也就是公元一四三五年,从赋税到后来在流通领域用银元币制。那么白银从哪里来?有一部分从日本来,后来哥伦布发现美洲,跟中国做生意,用白银换中国的丝绸、瓷器、陶器、工艺品等。……在哥伦布发现美洲之后的头三百年,他们从秘鲁、墨西哥等地掠夺的白银,起码有一半左右运到了中国”③。正因为国外的白银不断流入,才能支持中国实行银元币制。我们过往印象中晚清的闭关锁国,并不是确定无误的事实,很可能只是某种被反复告知的结论。《潮汐图》当然并非为了证实这个结论,但作品本身展现的中外交流情形,可以让人们充分意识到问题的复杂性。
从《潮汐图》相对集中的这个时间节点,我们能够发现,在此之前,中外之间的交流已经很复杂,甚至很多外来的物件和风习,已经影响了土著生活的基本风貌,“福音船吐出两个人,一个番鬼传教士,一个番禺通事(同时还有助手、学徒、船工、厨师、花王、打杂)。两个人将烂瘫荣铲进担架、抬入船去。那担架是从巴黎流出的旧货,曾有十二个法兰西人、五个德意志人、五个丹麦人和三个匈牙利人于架上殒命”④。与此同时,巨蛙的命运更是跟与西方的交流相伴随,包括苏格兰博物学者H在广州的诱捕,包括他携带巨蛙至澳门生存,包括那些路上的风景和不同人物间的交流,都有双向的文化交流景象,因而小说也呈现出浓厚的开放气息。
这个开放气息,不只局限在书中所写的时代,而是通过虚构的巨蛙,走向了我们置身的时代。《潮汐图》中的社会交流和转变,并没有在作品结束时戛然而止,而是让我们意识到,当下诸多问题是当时问题的延伸或变化,提示我们反身思考我们置身时代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