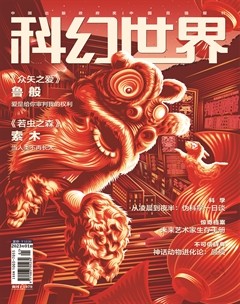汪旭:鲁般老师,你好!很荣幸请到你来我们《科幻世界》杂志的作者访谈栏目做客。这次参与访谈的还有我们杂志社IP部门的姗姗老师,她主要从事原创科幻IP的推广及改编工作,也会对你提一些有趣的问题!
鲁般:大家好,我是鲁般,很高兴和大家聊天。
王姗姗:你好,大家的老朋友鲁般。你好,阿旭。(大家应该记得《新贵》的女主角叫什么吧?)
汪旭:哈哈,一个美丽且意外的巧合。现在,鲁般老师已经算是我们杂志的常客啦!让我们先浅浅回顾一下光辉过去(笑)。你是2019年以长篇小说《未来症》出道的,又斩获了2021年中国科幻银河奖最佳新人奖,可以说是备受瞩目。想问一下,你有没有感受到来自外界关注的压力呢?这对你有什么影响吗?
鲁般:这种题目的标准答案,一般都是“谢谢大家喜欢我”“承蒙读者厚爱”以及“压力就是动力”。诚然,这些也确实是我真实的感受,但我总觉得用这样的标准答案作答实在是无趣。那么,我誠实地分享一个在我被大家认识之后感受最明显的地方:我的作品某种程度上其实是半成品。
在微博、豆瓣和科幻世界的论坛,我看过很多对我的作品,甚至是我个人写作风格和创作思路的解读。有金句频出的吐槽,也有长篇大论的探讨;有的会让我觉得如遇知己,也有的会让我觉得大可不必。但基本上都能自圆其说,就和高中语文试卷的阅读理解一样,他们把我写的故事展开成了一个他们期望的局面,就像一位大厨做了一道甜品为满桌客人呈上,有人吃出了大厨秘方里的南瓜,有人吃出了大厨根本没放的芝麻,有人甚至凭借某种口感判断出大厨的流派和故乡……这些并非大厨给予,而是食客们经由舌尖抵达大脑的感观创造。这样想来,甜品被大厨制作出来,其实只是完成了一半,不同的感受、深处的含义、特殊的回味,都是食客们消化后的创造,这才是这道美食的终点。我的故事在我写完之后,便已经跟我无关了,而读到它的人则在用他们的眼和思考丰富着这个故事:结局可以怎样、他还有怎样的选择、她是个什么样的人……这是个很有趣的过程,我甚至因为“鲁般一定是致敬了某某电影,模拟了某某作家的风格,复刻了某某历史时期”而真的去看了那部电影、读了那些书、了解了那段历史。
我不认为自己的作品伟大,但我认为,因为自己的作品拥有这样的经历是伟大的。因为这是一种极为特殊的成长,他们看到我写的想到我没提到的、读出我没写到的、写出我没想到的,最终,我的故事有了无数的风貌。这是在成为一个作者后,最让我着迷的人生境遇。
汪旭:我能理解你说的这种获得。一些在创作之初并未想过会获得的反馈丰富了故事,也让你看到故事坠入现实世界激起的涟漪。我想,不管哪个作者都会见之不忘的。我们看到你很快就调整了自己的创作节奏,从擅长的中长篇小说转到短篇小说的创作上,2022年在《科幻世界》杂志上刊登了《白色悬崖》和《候场》两篇小说。在你看来,创作短篇科幻小说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体悟?
鲁般:首先,我也没有擅长中长篇啦……其次,我也要实现一下上刊的梦想啊!回到正题,或许你们也发现了,我的短篇小说短都短在“时间”上,大体都是发生在一天、几小时,甚至几十分钟里的事。或许是受到一些短篇小说家的影响,我颇爱这样以小见大且极富冲突的尝试,让你细致地打量几分钟,通过一个固定的场景、两三个简单的人物,展示一段截然不同的未来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