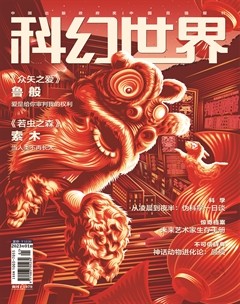春季第二旬的第五或者第六日,是一年中潮水涨得最高的日子。神庙的阿爷曾跟我们讲,每年的雨节就在这一日。第三轮也就是最大的那一轮月亮刚行过轨迹的顶点时,第一轮月亮正好在南方接近高处,它们神圣又美丽的身体吸引海水,海水就涨了起来。在这一天,它们的吸引加起来最强,所以潮水涨得最高。
和潮水一起来的,还有游鲸。
游鲸不是游在海里、黑乎乎的笨重生物,它们要庞大得多,有着半透明的浅蓝色躯体,高高地漂浮在天空里。每年的雨节之后——有时就是在雨节当日,成群的游鲸从西边大海的上空游过来,在附近的上空盘桓、游闹,像冬季的云彩一样,遮蔽整个天空。在合适的时候,一些游鲸向天空的上方游去,另一些则转头回到大海的上方,第二年再回来。
这时,镇上的人们就要忙着完成最后的播种了。因为游鲸走后,春雨就要到来。
春雨和其他时候的雨水不太一样。它丰沛但不泛滥,格外有效力。雨水普降大地,播种下去的种子会飞快地发芽。不出两旬,这些种子就会长出半人高的苗,再过四旬,就可以收获香甜的藜米。若谁家的懒汉错过了这一时节,就不得不靠申领神庙的救济挨过这一年。勤劳的人家只要播种完成,再在冬季前按时收获,就可以悠闲地度过炎热的夏日和漫长的冬季。
那时候的雨节就是美好一年的开端。
十二岁那年,我在神庙上学。那年的春假,因为家里的人手够多,不需要我帮忙,于是我每天跑到校舍里看书、做雕工或者去活动室做模型。
阿爷是神庙派给我们的老师。他的胡须很长,早已变白,一条银色的项链挂在他脖颈的棕毛上——那是祭司的标志。平常他给我们上课,并留守在学校里照看校舍。我念书有不懂的地方,或者碰到不会雕的细节,就去找他。
那天我正试图雕一个游鲸群的图案,阿爷过来找我。
“米米,不要这么用功。今天是雨节,码头有集市。阿爷走不动了,你去帮我买点儿糖米回来。”阿爷笑眯眯地给我塞了几个铜板,“不用着急回来,今天的表演会很好看。”
“好嘞!”我知道阿爷只是怕我孤寂,想让我出去玩一会儿。我的确雕得倦了,要休息一下。
跟每年的雨节一样,码头上挤满了人。我看了一圈实物和表演,都不怎么感觉新奇。我买了一袋糖米,又买了肉干当作午饭,在码头平台的栏杆边坐下,看着大海发呆。我坐在这里,倒不是为了躲避人群的喧躁——虽然我确实很不喜欢人群,只是为了等待海面上的表演。
码头总共有三层。最下面一层的高度和雨节这天的海平面持平,此时已经搭上了浮板,作为表演的舞台。神庙领舞人婆婆带领表演者等在一边,我看到高年级的几个伙伴也在其中。
雨节的庆典有非常盛大的演出。再晚些时候,这里就要人满为患了,而此时还有视野最好的位置。
太阳轨迹行至地平线上方后五分之三段起点的时候,庆典就开始了。
庆典以一声呐喊引领的歌声开始。当歌声淡下去,微弱而低沉的鼓声笼罩了安静的码头。开始的几个舞蹈描述的,据说是宇宙的生成、天空的出现和大地的诞生。绀色、绛色和墨绿色的长袍披在舞者的身上,细密的节奏自他们的足下踏出。这些舞蹈抽象且精致,需要许多年的练习才能掌握。接下来的舞蹈更为复杂,无法用语言描述它们,至今我都不理解它们的全部含义。
当舞蹈告一段落,一个铁制的圆环从海水里升起来,周身燃起火焰。海里又翻出了一艘载着人的舢板,表演者逐个跃过铁环,跳到码头上。轻快的乐声响起,围观的人们也发出大声的欢呼——新一轮的舞蹈开始了。阿爷曾告诉我,铁环象征着玛神的手镯。玛神游过星星做成的大海來到大陆上,他将手镯扔在地上,人类的祖先就从中跃出来,繁衍生息。
那一年的第一群游鲸就是这时候到来的。
当象征手镯的铁环落回海里,人群的欢呼声还没有平息时,便听到有人欢叫起来。
“看,游鲸!”
我们抬起头,望向西南边的天际。是的,那片蓝白色闪着太阳光芒、好似倒置大海般的集群,就是鲸群。人们再次欢呼起来,连演出者都抬头仰望。人们议论纷纷,鲸群准时到达是天大的吉兆。欢乐的气氛里又多了几分狂欢的意味。
鲸群游得更近了一些,尽管它们的身体是半透明的,但现在可以用肉眼逐个分辨。游鲸大体上是水滴型的,侧面有翼鳍,还有一条长长的尾鳍。它们的身体里能看到许多椭圆形的空腔,一些是浅蓝色,更多是透明的。透明的球腔会随着游鲸的游动和沉浮,周期性地收缩,节律舒缓而安宁。阿爷讲过,浅蓝色的是游鲸身体里的水,透明的是一种轻捷的气,水供它生存,气供它漂浮。它们离不开水,正如人离不开血液;它们离不开空气,正如人离不开大地。这一年的鲸群,为首的是一只头上有一道黑纹的游鲸。我听到有人说,去年它也在第一批到来的游鲸里。
我一直呆呆地望着鲸群,没有注意到几乎演变成狂欢的庆典是如何结束的。鲸群越过镇子,最后停留在东北方向巍峨群山之上的天空中。那时天已经擦黑,我背起糖米袋,转身走向神庙。
春天的晚风吹拂在街上。进入学校的洞口之前,我揉了揉酸涩的眼睛向东望去,忽然注意到那里有个闪亮的圆环。这是最小的月亮希尔曼支吗?不,它看起来比希尔曼支在这个季节通常的大小还要小上一半,换作眼力不好的人甚至看不清楚。而且,我努力地回忆自己贫乏的星相学知识——不论月相,希尔曼支此时应该还没升起来。
这是什么星星呢,或许只是一只落单的游鲸在夕阳的余光中显出的轮廓?我还没有来得及想得更多,校舍的大门打开了,阿爷正在迎接我。我立刻将这事儿抛诸脑后,直到两旬以后。
不出几日,天空就被鲸群占领,不再留下一丝空隙。就算是在中午日光最盛且云朵稀疏的时候,阳光也只能透过游鲸的身体落在地上,蓝色的波光在地面不停地浮动。鲸群停留了一旬后,过了几日,天空聚集起一些云彩,一些游鲸朝着西方慢慢地游回大海,余下的便向上游去,融进云里。许多年以后,我才有机会更近距离地观察这壮观的场景。但当时,别说我们,就连阿爷也不知道这些鲸去了哪里。那时我想,天空之上也许有别的地方。大地上有天空,天空上不也应当有更高的空间吗?蓝色的天穹看起来不太像有固体约束,那里大概有什么比空气更轻捷柔软的东西,说不定正是游鲸身体里的气呢!或许它们要去那里补充这些必要的气体?阿爷总是笑眯眯的,对我这些小小的哲学思考不置可否。
游鲸离开后,雨又下了接近一旬。直到雨节过后整整两旬,天空才终于放晴。
这时,我才想起来雨节那个晚上我的发现。事后大家比对起来,我似乎是第一个见到那颗星辰的人。但无论如何,现在几乎每个人都能看到那个闪光的圆环了。
它的出现,起先引起了不小的惊慌。
谁也没有见过这样的星星:它不像月亮有相位的变化和明暗的纹路,几乎总是一个圆环,没人看得到圆环中间是什么。这不仅仅是因为它小——阿爷私下告诉我,即使是神庙的祭司们用祖传的远望镜,也看不清圆环中间有什么东西。不过,这颗遥远的星星似乎并未影响镇上的生活。古老的星相学法则,亦没有提及这样的凶兆。既然人们与它相安无事,便也慢慢地淡忘了它的存在。只有偶尔在天文课上,我们会吵着让阿爷在远望镜里寻找它的踪迹。
人总是容易遗忘的。
平静的生活持续到我十七岁那年。我从神庙毕业了。我没有像哥哥那样回家管理庄园,也没有进入殿堂继续学习神学或者去某个工场工作。我向祭司们提出,想进入神庙的工坊研习。我想做一架飞行器。
大部分祭司對此没有兴趣。在那天的议事会上,他们焦虑地谈论着别的问题,几乎不愿讨论我的想法。好在阿爷一直支持着我。在他的帮助下,我在工坊找到了一个职位。
这想法不仅源于对游鲸的痴迷。那一年我在神庙的图书馆里找到了一本书,上面记载着一种名叫热气球的飞行器的制法。它的原理非常简单,取防水的鱼皮布做一个足够大的口袋,口袋下连一个载人的篮子,篮上架一个火盆。口袋的内部由火盆加热空气,使它变得又热又轻,飘浮在空中,正如游鲸之飘浮于天空,也如船之漂浮于大海。我们说,天空和大海别无二致。
不仅如此,书里还记录了许多细节,使这一切看起来能够实现。例如,制作什么样的口袋形状使热气球不容易倾覆,用什么样的火盆能控制气球的上升和下降,怎样在不同的高度寻找风来改变行驶方向。不过,作者写道:“虽然我们于古老的经典中录下这些方法,但据我们鄙陋的见识,还没有人成功地制作出这样的装置,使人成为游鲸的同列。”
既然还没有人制出这样的装置,那么是谁、他又如何书写了那些“古老的经典”呢?这种深奥的历史和神学问题,长久地困扰着人们。而那时,我更关心它如何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