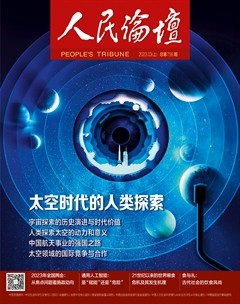【关键词】宇宙探索 太空资源 深空探测
【中图分类号】P159 【文献标识码】A
大约5300年前,河洛古国的观星者用九个陶罐演绎出“北斗九星图”,该图不但反复出现于同一时期的文化遗迹中,还在后世许多史料中留下只言片语的记载。结合这些线索和九星中的两颗如今已消隐不见的事实,历史学家和天文学家经多方考证,共同确认这是对天球上位于“北斗七星”两侧的两颗超新星遗迹的记载,也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超新星遗迹记录。事实上,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有着不同形式、不同语言、不同先进程度的天文学相关记载,让我们可以从中抽丝剥茧出更多有趣的信息。将这些信息汇总起来,就构成了一部人类天文学发展史,亦是一本人类探索太空的远征日记。人类对于日月星辰的好奇、崇拜,对其运行规律、来源和终点等问题的思考总结,以及在探索这些奥秘的过程中所做的一切正确的、错误的点滴尝试都被记录在内。
裸眼观星时代:不同文明天文学发展呈现出同步性
随着人类对天体的观测逐渐日常化,记录范围和重点也逐渐从日月扩展到太阳系内的行星和明亮的恒星。例如公元前17世纪左右,古巴比伦城邦中人们用楔形文字将金星的运行状态记录在泥板上,这是最早的金星运行记录,在之后出土的泥板中,也发现了对其它行星的观测记录。公元前15世纪,殷商中兴之主太戊帝的得力助手巫咸,凭借其丰富的观测经验,以北极星和华盖星等为指引,创造出航海观星定位的牵星之术,提出“指”这个牵星概念。后世的《巫咸占》《开元占经》等皆传承巫咸之学,以及它的星占占辞和星表。与此同时,在隔着半个地球的尼罗河畔,古埃及神庙的高级祭司们手持麦开特(古埃及人特有的天文测量工具)虔诚地记录着众星辰的位置。不远处的宫殿里,皇家天文学家、哈特谢普苏特女王的宫廷主管塞内姆特尝试着将他对行星的观测记录融合进自己的建筑设计中,使我们得以在3000多年后,于女王神庙的传世壁画中一窥前人的浪漫——譬如牛首人身形象所代表的木星,钩子或鹰所代表的金星。
在不同文明均开始关注金、火、木等行星和一些明亮的恒星之后,大家似乎又心有灵犀地意识到总结天体运行规律和制作全天星表的重要性。大约2400年前的战国时期,在诸子云集的齐国稷下学宫中,鲁国人甘德尝试编制全天星表,并发现岁星(木星的古称)的一个特征为“登若有小赤星附于其侧”,这是现存对木卫三观测的最早记载。甘德根据对木星观测规律的总结,创造了甘氏岁星法。差不多同一时期,魏国人石申提出了改进的岁星纪年法,并结合大量观测记录绘制了全天星表。到了公元前2世纪的西汉时期,人们将二人成果总结为《甘石星经》,收录了大约800颗恒星在天空中的方位及運动规律,成为最古老的天文学著作之一。巧合的是,此时小亚细亚半岛一带,希腊人喜帕恰斯诞生。他经过在罗德岛的长期观测积累,绘制出依巴谷星表,收录了全天1022颗恒星的方位,是西方最早的一份全天星表。又过了几个世纪,三国时期吴国天文学家陈卓横空出世,集甘德、石申和巫咸三家星表之大成,总结出中国古代经典的283星官1464星的星官系统,对后世影响颇深。
公元1世纪,东方大地诞生了张衡,西方大地诞生了托勒密,二人皆为天文大家,对天文学有着深入且系统的认识,并且都结合前人的积累和自身的研究,对天地形态和各种天文现象给出了基于数理学的解译。当然,二人的观点不尽相同,托勒密撰写《至大论》,主张“地心说”,认为日月星辰绕地而动,而张衡则主张“浑天说”,认为“天之包地,犹壳之裹黄”。细思过后,我们可以认为两种学说在星辰日月绕地而动这一点上大致相似,只是形态理解上有所差异。总而言之,公元元年前后的几个世纪,经过长期的天文学资料积累,不同文明中各自诞生了集前人大成的天文学著作,这是一次天文学发展的同步。此二人主张的学说都在各自的地域统治后世千余年,直至历法误差在10多个世纪的岁月里逐渐积累到了无法使用的程度,才逐步被质疑和取代,而那个时候,世界各地的文化融合已然开始,同步也就成为了一个必然结果。
望远镜观天时代:人们生产生活需求推动了天体测量学的繁荣发展
文字的诞生让人类的经验得以横向传播和纵向传承。伴随着日、月、行星等天体的观测资料的不断积累,它们的周期性运行规律被提炼出来。人们随即应用这些规律来更好地改善历法、提高生产力,这其实就是古巴比伦人绘制日月运行表和甘德、石申等天文学家总结行星运行规律的社会驱动力。对于不同文明而言,这种需求的强烈程度大体一致,且人类群体能力的上限也大体一致,这就导致了不同文明花费了大致相当的时间达到了大致相同的文明发展高度。这一点在之后也得到了认证——当行星的规律逐渐揭开时,对于一些细微的误差和无法解释的现象,人们开始将希望寄托于更多的天体参照物,也就是说人类社会活动自发产生了确定天体准确位置的需求。这也是为什么在公元元年前后,东西方科学家都在努力交出全天星表答卷的原因。在观测和绘制过程中,他们对日月星辰的运动进行思考和总结,分别诞生了影响其所在区域千余年的天文学理论。
哥白尼逝世后的第三年,丹麦天文学家第谷·布拉赫诞生。他是历史上唯一可以与喜帕恰斯一较高下的肉眼观星者,一生致力于天体观测,并在逝世前将自己十数年的观测成果交给助手约翰尼斯·开普勒。开普勒早年已然接受“日心说”思想,他综合第谷的数据,总结出行星运动三大定律,被称为“天空的立法者”。同一时代,哥白尼理论的另一位拥护者——伽利略·伽利雷使用自制望远镜观测天空,开启了探索太空的新时代。伽利略不仅发现了木星的四颗卫星,记录了太阳黑子、金星盈亏等天文现象,还在数学、物理学上具有极高的造诣。他亦是独步于时代的斗士,勇敢地宣传哥白尼的“日心说”理论,顶着教会巨大的压力,写下了《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轰动了当时的科学界,被誉为“现代物理学之父”“科学方法之父”。
伽利略去世的同年,在英国林肯郡一个名为乌尔斯索普的小村庄里,艾萨克·牛顿诞生。他建立了完整的牛顿力学体系,发现了万有引力,分析了潮汐现象与日月运转的关系,预言了地球不是正球体,等等。这些新观点、理论以及研究方法的开创,对天文学的发展影响巨大。牛顿对天文学的另一项伟大贡献是他成功研制了反射式望远镜,使欧洲天文学的发展突破了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仪器限制。自伽利略开始,人们一直在尝试制作更适合天文观测的望远镜——在当时的认知里,那就是更大的折射式望远镜。为了尽量减少折射式望远镜的色差,需要尽量降低透镜曲率,这不但对磨制镜片提出了更高的工艺要求,同时也使成像焦距进一步增加。因此,在大约60年的时间里,天文望远镜的镜筒长度以匪夷所思的速度增长。例如,当时已制成镜筒长达45米的望远镜,人们甚至需要另外建造一座高塔来支撑它,而观测者在使用它时需同时调动百余人调整望远镜方向。可见,这样的庞然大物即便具有优秀的成像能力,也因为笨重而很难满足观测需求。荷兰著名的物理学家、天文学家、数学家克里斯蒂安·惠更斯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他创造性地抛弃了镜筒,设计出“天空望远镜”,即观测者手持目镜站在数个街区之外,结合安放在远处高塔上的巨大物镜进行观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