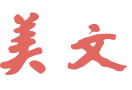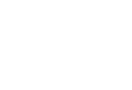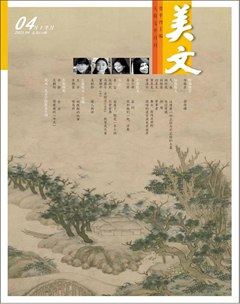舞 台
舞台是水上舞台。
数百名观众围在舞台下观看舞台上的表演。我被挤在人群之中,浑身被挤出酸溜溜的汗臭,双脚几乎被架空成一对悬挂的火腿。
舞台演的是一个王带领七八个武士与河妖抗衡的故事。王轩昂立于圆形舞台正中央,武士在四面转圈奔跑,随后迅速向王靠拢,用蛙跳型的双手将王托举至半空。王集权力与巫气于一身,披着粗布风衣,身材魁梧奇伟,背负着黎民百姓的期盼。王将长杖刺向天空,使出一个霹雳打雷的动作,引来闪电震慑河妖。
王面露凶色,鼓着嘴腔向河妖喷出熊熊的大火。我身旁有一个扎着辫子的小女孩,她被吓得发愣,忽然回过身来埋进妈妈温暖的怀抱。妈妈立即用手捂住她的头,说不怕不怕。小女孩却又转身将目光重新投向舞台,欢快地指着舞台上的王说:“妈妈,妖怪!妖怪!”小女孩与我当年一样,分不清谁是好人,誰是坏人。
河妖掀起巨浪,鬼一样狰狞的头部浮出水面,张开血盆大口,欲要吞没过往船只游人。王再次将长杖刺向高空,几道闪电劈入河妖嶙峋的脑门,河妖遁入水里。
这是流传于当地民间的一则传说故事。据说,这只是其中的一个剧情,往下的剧情还包括一对阿哥阿妹在王的庇佑下喜结连理,产下哭声洪亮的婴儿,打开鲜活的人间幕布。
舞台表演是热闹的,可我爱往热闹里挤,爱舞台上漫卷的烟火,爱人间的传奇故事。有时候半夜做恶梦醒来,觉得人好不容易活着,我不能把自己往孤独和寂寞里赶,过着牢狱式的生活。一个人随时都可以在菜市、大街、商城瞎逛,在街边餐馆、火锅店、烧烤摊就餐,在红白喜事的席间喧哗或悲恸,才算握住最具烟火味的生活。
我真切需要这样的热闹,白天帮助我度过昏昏沉沉的日常,夜晚助我抚平纷乱如麻的思绪。我看见除了小女孩之外,人们在舞台底下挨挨挤挤,他们和我一样,都在伸着脖子向舞台索取故事。我们立起脚尖,睁大双眸,绷紧着脸皮,呈现生命的每一处寂寞、惶惑和饥渴。我们大都过着黑白色的日常,那些具有饱满色彩的日常,需要我们出门去寻找,去到舞台、去到野外、去到海平面、去到高峰、去到丛林、去到人群、去到荒地,去到梦境、去到意识的边缘地带……
我们害怕孤独,极度渴望热闹。我知道我刚出生之时,肯定热热闹闹地哭过,向世界宣告生命的开端;在二三十岁的年纪,我奔赴一场热热闹闹的婚礼,开始走向人生的拐点;外祖母逝世的那一天,我看到一群人围在她的躯体周围热热闹闹地哭。人生的每个阶段都是舞台,它上演我们的出生、婚姻、死亡,以及善恶、美丑。它是如此贴近我们的一生。而我们一贯以为幽静是审美场域,更多的时候不愿意接纳热闹,认为热闹是俗气,是吵闹,是打搅,它破坏了美的氛围。
我和瑾已步入而立之年,然而我们的婚礼迟迟没有办成,母亲很着急,她已连续三年催着我和瑾办酒。父亲逝世后,母亲寡妇的“身份”使她在村里抬不起头,她需要我和瑾的婚礼来证明她这一生是热闹的,而非沉寂的,因为她培养了这么出色的儿子——她曾经向村里的人炫耀她的儿子在某某局机关担任重要工作。她还分别向大姑、大伯那里借来几万块钱,把老家的房屋装修了一番,体体面面地用来做我和瑾在农村的婚房。我们的婚礼能扫荡她过去十二年所受委屈,成为她人生大放异彩的舞台,然而疫情没结束,我和瑾就没办法办酒。后来我想走折中的办法,提议简单办,只请几桌亲戚到场。母亲说,那怎么成?几桌人,那还叫办酒吗?
民间需要故事传说,落实到具体生命个体,则需要热闹。母亲年近六十,守寡十余年,我知道我终究拗不过她,她和那个小女孩一样,有向舞台索取热闹的权利。
商 场
裹着浑身的汗臭味,夹着似散未散的烟味,我从人群抽身离去,走上二楼的民宿房间。
离开餐桌时,还有半杯白酒立在我面前,一颗炒熟的花生米掉落在杯里,浮起一层泛光的油花。从下午四点喝到现在晚上十点多,我实在喝不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