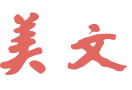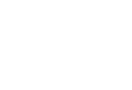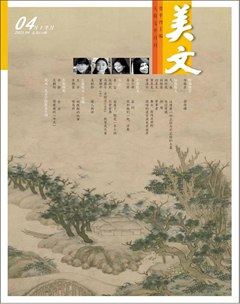前段时间在书上看到鱼类有一种特殊的运动形式,叫洄游,这是一种有规律的往返迁移,贯穿着鱼的生命始终。我的成长从来没有离开过西安,从家到学校,再回到家;从西安去别的城市旅游,再回到西安;从冬天游到温暖的春天里,再回到最熟悉的雪地……剥落旧的外壳,再一遍遍洄游到过去,周而复始,好像一直都在原地,又好像是绕着这个原点画了一个又一个的圈,但就像有些洄游的目的和路径并不一样,每圈和每圈也是有所不同的。也许这种圈跟树的年轮一样,也是生命的一种行进轨迹吧。
我喜欢冬天,要是谈到我的冬天,就必须谈冬天里的树。在北方,最常见的树在冬天都脱了枝叶,光秃秃的,直指着天空,那姿态有时候是一道优美而流畅的曲线,是美人低头时无意间露出的一截雪白的脖颈;有时候是戛然而止的,是生硬的,是文人嘴下冷峻的纹路。它的树枝是国画里最经典的鹿角的画法,每处枝节的拐角,都是笔墨停顿手腕用力的一笔;它的树干也不需要点苍,自然布着岁月的霉点和风沙的刮痕。这是我现在最常见到的树,不过,以前的树是不一样的。
初中的时候,学校的操场旁种了很多树,只有到入冬的时候,树叶才真正大片大片地往下掉,给人一种迟到的秋的错觉。铺在地面上厚厚的一层,刚小心翼翼地踩上去,落叶底下就发出些簌簌的声音,好像惊扰了鱼的美梦,然后这些声音开始在脚下飞快地游动起来,脚的触感变得绵软湿滑,惹人发笑,止不住的快乐从脚底往上窜。要是积了厚厚一层雪,脚下的世界就更丰盈了,一个脚印下去,身子就往下一陷,雪是坚实的,地面是湿软的,好像踩在两个世界的交界处。要是世界颠倒过来,我猜鱼在水里游的时候,看到水草和漂浮的树枝可能也会觉得那是树吧。
我和我的朋友就像思琪和怡婷,我们爱文学,雪就是我们最好的启蒙老师。雪填满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就用所有我们能想到的天马行空的修辞填满冬天。下了晚自习,我们往人潮的反方向走,在喧闹的人群里,我们是一模一样的两个,却又和别人迥乎不同。有时候笑着闹着,有时候则肃穆着赶路,我们有要紧事要做。走进操场,世界骤然间就安静下来了,树干上贴着便签“这是雪国”,肃立了一会儿,屏息凝神地往里走。我们步子迈得轻,可每一步落下,脚下还是会发出雪被压实时“吱呀”的碎响,有声音的人走进了没有声音的世界。
雪地在月光下格外地亮,我们谁都没有开口,明明走在操场上,我们却好像顶着风雪,走在只有我们两个人的雪地荒原上,有时候亦步亦趋,有时候相互搀扶着,心里有只火炉噼里啪啦地烧着。为了排遣赶路时的寒冷和寂寞,我们常在手里攥上一小团雪,一遍遍地把它握紧,压实,等到雪球完全变成一个坚硬的冰球,手心变得滚烫起来了,我们就立马把它往火炉里甩去,加上一把炭火。慢慢地,雪下得越来越大,覆盖了所有声音,我们没有任何顾忌了,卸下了所有的戒备和包袱,我们变回了两棵树,变回了雪花电视机里的两个噪点,变回了最纯洁最无知的孩子。我们在雪地里又跑又跳,然后猛地扎进雪地里打滚,然后以坠落的姿势仰面倒进雪地里——雪地是猫咪腹部紧绷而柔软的触感,或者说,来摸摸我的心吧,也是我抚摸猫咪时心脏的触感,一戳就陷进去一个小坑,然后慢慢地回弹。
躺在雪地里看着天空,我的身体变成了一小片湖泊。天真的好黑啊!书上说,只有很少一部分人的眼睛是纯正的黑色,我以为自己就是那一小部分人,还为经常收到的关于头发和眼睛乌黑的夸奖感到窃喜,后来发现我的眼睛在阳光下是隐隐的红棕色,头发也是,不过我并不难过,转头又为这独特的另一面感到骄傲去了。酥麻的寒意像鱼一样游过了身体的每个角落,但是湖水始终没有结冰。
这时候的天空是我从前的眼睛,一朵朵雪绒花从无垠的黑色里缓慢而坚定地落下来,像一曲悠扬的牧笛。哼着、唱着,我们交错的视线和树的枝桠拉成了歪歪斜斜的五线谱,雪下大了,从五线谱里纷纷地落下来,变成了无序的音符,在深夜里缓缓地游荡。压在树冠上,树白了头,以一种果实累累的姿态虔诚地俯下身子;堆在树枝上,树枝成了一段莽黑的山脊;撞到树干上,就“叮”地一声磕掉一块树皮,露出一小块白色的芯,像刺猬的肚子一样在寒风里瑟缩着。我的一部分可能就是那个时候被磕掉了,永远地留在这个雪夜,深埋在柔软的雪地里,等着我一遍遍地洄游。
树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呢?两棵在霜风里并排立着的树,时不时笑得乱颤,叶子簌簌落满地,笑累了,就靠在对方身上歇一会儿。鱼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呢?两颗纽扣般的小眼睛,在水面上吐泡泡的声音也是铁板上滋滋冒泡的声音。有些鱼很神秘,像鳗鱼,年幼的时候就要经历一场长达多年的旅行,从马尾藻海游到淡水去,等到成年了,再循着这种在幼年时就深入它们身体的大海的气息游回海洋。
为了考上好高中,妈妈给我找了更好的补课老师,不过那地方很偏远。上完课的时候,我们赶着公交车回来,车里人很少,也没有人说话,在一整首小夜曲里,只有车厢慢慢悠悠晃荡的声音,不断碾过松动的井盖、落叶和一些细长的车辙。因为路远,我们不用盯着还有几站下车,不用去想是把中午的饭热一下还是煮个泡面,不用赶作业收拾第二天的书包,在这个车厢里,强势的母亲和倔强的女儿疲倦地靠在一起,女儿的摇篮也成了妈妈的摇篮,女儿的美梦也是妈妈的美梦,女儿感受到的树啊鸟啊鱼啊,不爱看书的妈妈在梦里悉数梦了一遍。
妈妈没有感受力吗?妈妈不爱美吗?妈妈不可爱吗?妈妈始终是世俗的人吗?我那个时候不懂,但是我以为我懂。我以为我懂很多道理,但是書和长辈们没有告诉我的是,道理只有真正经历了才会理解。
她们挨得很近,手臂像脐带一样依恋地环绕着,黑白的树影和灯光像飞鸟一样在她们脸上掠过,好像被时间赐予了某种剥夺的权力。光和影实在是太神奇的东西,当光落在母亲脸上的时候,她的脸砰地一下饱满起来了,她平时总是蹙着眉,可当她真的熟睡了,卸去了母亲这个身份,那道皱纹变成了一道浅浅的光洁的疤痕,像是阖起来的第三只眼;光落在女儿脸上的时候,则显示出岁月对年轻的苛刻,眼下郁积的青色,鼻翼浅浅的纹路,脸颊上的色斑,这些常人看不见的东西,这些她在镜子里苦恼的东西,在光下显得异常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