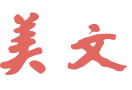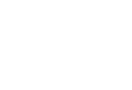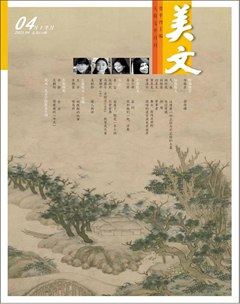2021年6月25号,发完《不想告别的告别》一文之后,有那么几天我发现自己突然炙手可热——许多朋友的慰问电话短信过来。纷纷问我需要什么样的帮助;还有热心人牵线搭桥,让我竟然有了一种可以绝地逢生的错觉。后来才发现,错觉就是错觉。我最后的一搏,变成了更加可笑的笑话。
于是索性就真的回到家乡自贡,那几个月,并没有真正地哭一场,睡不着倒是真的。当我终于把自己安顿在自贡乡下一间河边的小屋时,我发现是如此的合适:没有一个认识的人,也就没有向任何人解释我命运跌宕的必要。推开门,目之所及,不是田地就是河水——与密不透风的高楼大厦比起来,这些让我在落魄中体验到新鲜的陌生感。
我当然想好了自己要做什么,仙市镇是我特意从备选的三个镇里面挑出来的。隔壁的王瞎子形容“划一根火柴的工夫就能在镇上转一圈”,没有书店、图书馆、咖啡馆,自然也不会有电影院,美团、盒马在这里是无效软件,当然也不会有滴滴——这几乎就是我想找的那种既可以快速切断过去,又可以在陌生感中收揽注意力的地方。
刚来的第一周,我需要和一只巨大的原住民蜘蛛斗智斗勇。在城市里长大的我,从来没有看见过尺寸如此惊人的蜘蛛,我甚至觉得它的体型,已经远超阳澄湖大闸蟹。小窗看到照片说查过资料,这张脸应该是网红蜘蛛,叫做白额高脚蛛,不会伤害人,而且还会帮着对付厨房里的蟑螂。我每隔一个小时去看,它始终敛声屏气地呆在那里,简直就是一个安静的美男子,只是石化了,和时间比拼着坚硬的程度。
有天早上起来在客厅里面接了个电话,不知道怎么迷迷糊糊地眯了一会儿,突然好像有滴水滴到胸口,然后睁眼一看,原来安静的美男子突然掉到我身上趴着,我吓得一激灵,从沙发上一跃而起,拼命把它甩到地上。此后有整整一个月,我都需要在屋子里提前确定好它的方位,再据此来调整我的行动轨迹。
除了这个熟稔的“家养宠物”,天花板上还有一群神秘的动物,总在夜深人静时分万马奔腾,当然有的时候它们的生物钟也不太准确,就会造成午饭时分开始出现骚动不安的节奏,间或传来吱吱的声音,和一些天花板缝里漏下来的大颗耗子屎。
后来我想,或许这里的生活过于安静,以至于我对生活的观察可以精确到所有的细枝末节。从前的日子远去,没有人争相邀饭,也没有商业谈判和频繁社交,剩下的只有,各种银行贷款的频频问候。也好,我索性有段时间关掉了朋友圈,让自己沉潜进入这无人知晓、无人联系的河底。
后来看书,看到有一段写郁达夫在苏门答腊的辰光,因为“忘了门牌。他在阴暗的街灯下,来来去去地找了半个年头,敲人家的门,询问张德生的住家。直到夜晚二时要离开的一小时,他才放弃了他的希望,是什么希望呢?他只希望跟一个可以说话的朋友说上一声,我要回去下,黑夜两点钟的时候,我们要赶回西苏门答腊去了”。
也是从那时候开始,我意识到,来之前和师友讨论到“来写一本书,看看故乡小镇的女性如何生活”的想法,会是一条“茫茫黑夜漫游”的路。
居所门口有家“张羊子羊肉店”,每次路过都能看到一两只山羊,大多呆呆站定在那里,有次一只山羊四处觅食,垫起脚尖把靠墙的扫把吃了,我觉得很有趣,忍不住上去喊它一声,它立即看向我,咩了一声。
第二天路过的时候,门口却换成了一只白色的小山羊——羊肉店门口的山羊,命运早就注定了,这还有什么可说。我还是无端端有点难过,很后来我才知道,这仿佛是种隐喻——在这里,生命是如此地卑微,来去无踪。
到镇上没多久,一个女人自杀了,街头巷尾议论纷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