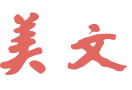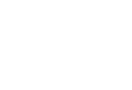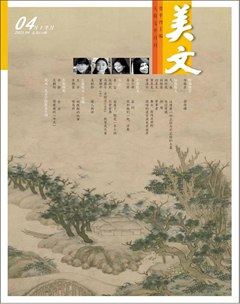船上唯一的主人
我站在一艘大船的驾驶台上。一个人站在我的身边,我看不见他的脸。船速有些超自然,那样的速度载着我们一路向前,我对那个人大声叫喊:“停船!停船!”我听到他回应:“你是船上唯一的主人。”这句话顿时让我惊慌失措,我们的船进一步增速,我绝望地朝四面八方观望。我怎样才能中止这场令人眩晕的竞赛呢?船骨犹如鱼雷一样滑行,仅仅在水面掠过,给我的印象是,只要稍有移动便会让我们倾覆。在某个时刻,随着我的目光在波浪上漫游,我看见浪峰上显现出人头。这片辽阔的水域是由上百万张扬起抛向无限的面庞所组成的。然后,我心怀恐怖地想到,我们盲目地飞速行驶肯定会撞坏并吞没那些面庞。然而,我也依旧心怀恐怖地意识到,通过打破那载着我们一路前行的平衡,要停下来甚至是减一点速,都会把我们抛进那一簇簇被淹没了身子的人头当中。“停船!停船!”现在颇有讽刺意味地轮到那个嗓音大声叫喊了。为了不去看我们将要不可避免地撞上去的礁脉,我的目光凝视着远方。我听到我的嗓音犹如回声一样回应着这个影子:“我是船上唯一的主人!”
最后一班地铁
车厢慢慢空寂了起来,在每個站点卸下更多一点它所运载的人类货物。我站在一个白日梦中,眼神迷失于一张张脸上。然而,坐过站的感觉把我从那种恍惚状态中唤醒,我准备在下一站下车,就在那时,我突然完全彻底地意识到发生了什么:这趟地铁再也不会停下。这盲目的列车载着意外的货物,沿着任何地图上都不曾标注的一条路线前行。我再一次看着那些脸。要是我不知道它们真正漠然的话,我就会相信,在这些不承认自己知道正在进行这场历险的匿名乘客之间,有一种心照不宣的领悟。最后旅程的伴侣!……毫无疑问啊!……没人给我选择:他们困倦或失败的脸上没有露出明显的预兆!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一如既往地继续交谈,但他们的嗓音流露一种察觉不到的细微差别。一个秃顶的胖子断然声明他的烹饪偏好:“你能在哪里找到上好的鹌鹑?在阿尔巴尼亚!”两个额头过大的孩子位于一个女人的两侧,那个女人疲倦地点点头,而另一个较老的女人则在她的前面喃喃低语:“我告诉过你,你一生都要抚养尸体……”距离这可怜的一家子两步开外,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动了动她那松弛的、涂绘过的嘴唇,仿佛她嘴里含满了苍蝇。突然,一个衣着寒碜的人站了起来,举起帽子,故意做出一种讽刺性的致意,用最大的声音嘲笑:“前往地狱的乘客们,上车了!……”这些话并未引起骚动,那个人重新坐下,再一次捂住他那张鬼脸。短暂的一刻之后,一个脸颊粉红、身着弄皱的老处女服装的大个子女孩,倾过身来向我坦白,说她在孩提时代就从公墓中偷走了一件小小的瓷花瓶。但这些话真正带着疯狂,并未阻止车厢那单调的声音一刻——在那条漫无休止的钢轨上,一节节车厢滑行得越来越快。
桥
有一座将要跨越的桥。彼岸就在那边,隐藏在一片从激流中显出的浓雾里。在这乳白色的屏障上,两个高高的、一动不动的哨兵显现出轮廓,仿佛他们自己就穿着雾霭的斗篷。一想到要对抗这两个卫兵,我就害怕得浑身冒汗,当我走近他们,他们也许会具有威胁性,不管怎样,我都无法回避他们的提问。“你从哪里来?”他们当中的一个会问。
我转身,仿佛这个问题确实在我的耳朵里响了起来。在我身后,是我走过的一条条路、一个个地方和一座座城市,那么多,因此我根本无法用几句话就描述出来。我从哪里来?从生命的夏天而来,从快乐的四肢伸展,身体变得健康的暖和的草甸而来。万物真的都在那种明显的静止下逃逸了?我们真的消逝吗?突然,你发现自己置身于一片封冻的平原边上,那里将被黑暗吞噬,被雾霭团团围在两个威胁的卫兵之间。“你从哪里来?你干过些什么?……”
现在,这座将要跨越的桥就在那里,这唯一的桥横跨在激流上,朝着一片无形的河岸而延展。另一个卫兵,甚至会用更可怕的嗓音说:“你到那边去干什么?”因为这座桥是边界,彼岸是另一个世界。为了从这边到那边,我不得不对抗那两个哨兵,而他们跟雾霭和夜色越来越融为一体。我知道我从哪里来,但怎样说明我想到那边去干什么呢?
我就这样跟自己沟通着,走近那座桥的起点,很快就发现自己距离那两个哨兵只有两步之遥,他们的黑色轮廓扩展,他们纹丝不动的身影开始让我安心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