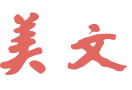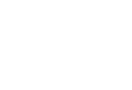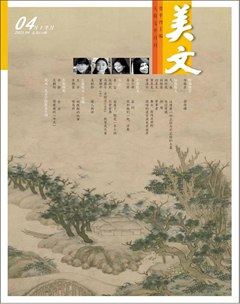如是,小方凳上堪称荤素搭配,浓淡相宜。一老一小推杯把盏,但听朱老头子漫说往事,颇有“前朝记忆渡红尘”之况味。
彼时窗外雪花纷飞。不远处传来火车的汽笛声,又有煤车缓缓驶进南站了。
在毛泽东还被人叫作毛润之的时候,有桩轶事恐怕鲜为人知,可我早在“文革”时期便听说了。谁讲给我听的呢?
朱仲硕,朱老头子。我曾经的忘年交。
当年蛰居长沙的朱老头子寂寂无名,但其家族却非常显赫。
扯远点,朱元璋是他的老祖宗,朱仲硕为第二十八世孙其来有自。明英宗时,封第七子朱见浚为吉王,建藩长沙。明亡后,吉王的后裔遭逢世变,为图隐匿,将“吉”字加“冂”改姓为“周”,潜入民间两百余年。
说近点,改“朱”为“周”的家族中,有个人叫周达武,少年时在宁乡石家湾挖过煤,后投湘军。因骁勇善战、军功显赫,深受左宗棠赏识。先后任四川、贵州、甘肃提督,手握重兵十数万。此周达武,即为朱仲硕的祖父。至晚年,周达武买下长沙城北的蜕园,这是当时省城内首屈一指的苏州式园林。清末重臣,两江总督魏光焘亦与之联姻,将女儿嫁给了周达武的次子周家纯。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湖南巡抚陈宝箴亦曾借居蜕园多年,其嫡孙,中国史学界一代宗师陈寅恪也出生在蜕园,比周家纯小七岁。
民国成立后,周家纯呈上家谱,请求湖南督军府批准恢复朱姓,改名朱剑凡。此人便是朱仲硕的父亲了。朱剑凡乃中国现代著名教育家,具有百年历史的长沙周南女中,即是他亲手创办。且将学校办在规模宏大的“蜕园”里,所以有“毁家办学”一说。年轻时候的毛润之,亦为朱家常客。朱剑凡惜才,经常周济毛润之。
再说近点,朱仲硕的二姐朱仲芷,为解放军的海军司令、大将萧劲光的夫人。小妹朱仲丽,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首任驻苏大使王稼祥的夫人,延安时代还是毛泽东的保健医生。来头都不算太小吧。
不无慨叹的是,朱老头本人却遭造化拨弄,乃至后半生潦倒不堪,走背时运。要不然,住在倒脱靴巷子里的我,如何会认得他?
先讲讲毛润之的那桩轶事。
对早年经常去他家的毛润之,朱老头记忆犹新。那时候,他才十四五岁的样子吧,“毛叔叔”经常去他家打秋风。或借本书看,或蹭顿饭吃。有次,他在自己屋里看书,忽然听到客厅里一声脆响。赶紧出去看,原来是一只青花瓷痰盂被打碎在地。又见“毛叔叔”慌忙跑出厅外,暗想,恐怕是他闯了祸,想开溜吧。但为了顾及毛的面子,便装作没看见。继而又发现门房进屋,将地上的瓷片细细收拾走了,更未在意。
待到晚上父亲回家,门房进屋告诉他父亲,方才知道事情原委。说毛先生打碎了痰盂急得要命,从长衫里抠出仅有的二十文钱,要他帮忙找补碗匠补痰盂。无奈碎得厉害,即便补好也得不偿失,且二十文钱远远不够,弄得毛先生好不尴尬。父亲听了大笑起来,说,不要他赔不要他赔!
此事亦有佐证,他的小妹朱仲丽晚年在一本书里也回忆过。毛在延安遇到她时,还提到说,我年轻时,穷得没有饭吃,是你爸爸叫我住在周南女校校园内,吃饭不让出钱,一天还吃三顿呢。
不过当时这个故事听了便罢,可不敢跟其他人说。
我跟朱老头子的关系八竿子打不着。年龄悬殊更大,那时他已经六十有六,而在街道小厂工作的我,才刚刚二十出头。记得初次见面,在那间四处透风的破屋里,他翘起双手的大拇指与小拇指,摇着说,两个六了!
所以认识,纯属偶然。且先认识的是朱老头的老伴朱娭毑。
那日,我去街道合作医疗站骗病假条。尤其听说换了位年轻的女医生,长得白白净净,样子蛮可爱,更想去一窥究竟,享享眼福。又想,若运气好,说几句惹女医生开心的话,或许还开得到一两瓶风湿药汀,可掺点糖精权当酒喝。
合作医疗站是“文革”时期的典型产物。先是在全国广大农村里普及,继而推广至几乎所有城市,一般由街道办事处管辖。医生大都是卫校毕业的,甚或还有仅经过简单培训的赤脚医生。也不要紧,无非看些伤风感冒之类,不会有人去看疑难杂症。街道工厂的工人那时无任何劳保福利,去医院看病不能报销,所以小病小痛去合作医疗站开几粒药便是,反正不要钱。
医疗站里有三四个人在候诊,都坐在一条长椅子上。我坐最后,有机会慢慢细细观赏那位新来的女医生。样范倒不差,但并非白白净净,而是白白胖胖,嘴角还有粒好呷痣,令人失望。正有些无聊,却看见从门口的逆光中,一位拄拐杖的驼背老娭毑踽踽走近,步子很短,影子很长。直至走到我旁边,尽管有个空位,却与我拉开距离,挨着椅角慢慢坐下。
我多少有点不忍,便站起来请她坐我的位置。老娭毑有点诧异,抬头看看我,说不用不用。我呢,既已起身,便霸蠻请她坐过来。
老娭毑拗不过,只好连声道谢,与我换了座位。
不料看完病,老娭毑慢慢走到我跟前,细声说道,你是个蛮懂礼貌的伢子呢。不嫌弃的话,欢迎来我家里来玩啊。停了一下又说,我家老头子可以教你学学英文呢。
这话说得我不好意思了。一时让座不过心血来潮而已,平时哪里晓得讲什么礼貌。但听说她的老头子会讲英文,倒使我有了好奇心。
老娭毑头发花白,满脸皱纹。脊背几乎佝偻成九十度,双手指关节则严重变形,形同鸡爪(如今知道,此即类风湿性关节炎的典型症状)。肘臂间挽一只缠满烂布条的塑料带编织篮,里头除了两茎莴笋,别无他物。但稍稍留意她的眼神,却显得既温和,又淡然。与一般街道妇女那种空洞、木讷的眼神完全不同。
加之老娭毑并非本地人,说话带有明显江浙一带的口音。
凭直觉,这老娭毑与她的“老头子”应该有点什么来头吧。尽管小有顾虑,但好奇心占了上风,便欣然接受了她的邀请。
不言自明,老娭毑便是朱娭毑,老头子便是朱仲硕了。
老两口子住在火车南站附近,毗邻煤码头的枣子园六号。
火车南站曾经是长沙最大的煤炭集散地。进工厂以前,十六七岁时候,我间或在此打打短工,主要是卸煤。通常是几个人包一节车皮,将煤奋力耙下,堆如小山。再由传送带轰隆隆转运至泊在湘江里的运煤船上去。印象颇深者,乃附近的街巷几乎全是灰扑扑的,空气中满是弥散的煤灰,居民白天皆不敢开窗。
先前,长沙城区的湘江东岸,以小西门码头居中,朝南北两向渐次延伸,布满了各类码头。左近的穷街陋巷密如蛛网。居住者多为城市贫民,且有各种街道工厂、手工业作坊混杂其间。枣子园即其中一条杂乱、肮脏的小巷。巷子尽头还有家新湘玻璃厂,我还在车间里看过工人吹电灯泡呢。
枣子园六号是栋砖木结构的老屋,两层楼。下半截青砖墙,上半截木板壁,已然破败不堪,现在想起来倒还有些特色。一楼是一家南货店,朱老头两口子住在二楼。木制楼梯居然不在屋内,而是紧贴户外墙壁,露天架设。虽有扶手,但颇为陡峭,一脚踏去吱嘎作响,初次上楼腿肚子不免发紧。
因平时见惯了太多挨批斗的各色人等,去朱老头家的路上,还设想了一下他的形状。一副谨小慎微、夹着尾巴做人的瘦老头样子恐怕八九不离十吧。未料爬上楼梯进屋,但见这个老头子高大挺拔,略显零乱的白发梳向脑后,额头饱满,面容清癯。眼神虽有些混浊,却暗藏一种逼人的光芒。其容貌与气质毫无颓丧之状。
见我站在门口迟疑,朱老头用一口喉音浓重的长沙腔朗声说道,我一看就晓得你是小王。請进请进,老太婆讲过好几回了。我有些拘谨地走进屋里,稍稍四顾,除一床一柜外,再未见什么像样的家具。显眼的却是一摞一摞码得半人高的火柴盒子,几乎占据了这间小屋子的半壁江山。
一边,朱娭毑高兴地抽了张矮板凳叫我坐下。落座,我跟朱老头搭讪道,你老是长沙人啊?朱老头竖起指头说,不光我是长沙人,我祖辈也是长沙人哦。又问我住在哪里,我告诉他住在小古道巷里头的南倒脱靴。朱老头子说晓得晓得,在南门口。长沙城里有两条倒脱靴巷,还有一条在臬后街,叫西倒脱靴,可一直通到药王街去。
我便小有得意地打算告诉他倒脱靴的所谓典故,与《三国演义》关公战长沙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