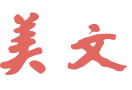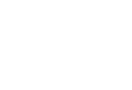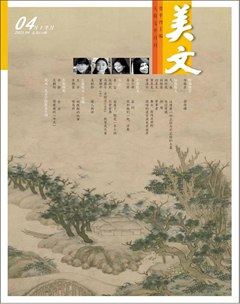九莉的幻灭
几年前读张爱玲的《小团圆》,读不下去,人物如走马灯,琐碎。最近又拿起来看,竟迷进去了,为九莉不值。花花公子邵之雍,怎配得上她的眼泪。
九莉就是张爱玲,邵之雍是胡兰成。离开上海二十多年后,在美国洛杉矶的一间小公寓里,张爱玲开始写《小团圆》,彼时她55岁。大约作家都会有一本自传性的东西,自己写也好,授权别人写也罢,总是个交待,省得身后被一些不相干的人说三道四。
不知张爱玲写的时候有没有犹疑,完成后她倒有些小心了,一度想销毁它,原因竟是不想让那个人得意。
她在给友人的信中说:
“《小团圆》是写过去的事,虽然是我一直要写的,胡兰成现在在台湾,让他更得了意,实在不犯着,所以矛盾得厉害,一面补写,别的事上还是心神不属。”
55岁的张爱玲已经能够站在远处看自己,一如她躲在绛红色帷帐后露出的幽深的、冷冷的目光。年轻时的冷是冰,化成水,到底是流动的;现在的冷是幻灭,爱情、恩情终抵不过世事流转,沧海桑田。
“我在《小团圆》里讲到自己也很不客气,这种地方总是自己来揭发的好……”这是张爱玲的洒脱,也是无奈。她知道她与胡兰成的情爱必将成为世人茶余饭后的谈资,文字里没有避讳。九莉与邵之雍由相识、相恋到结婚、分手,其间两人的芥蒂、猜疑、闺阁里的小秘密,都以张爱玲式的笔法呈现出来,写得很淡很淡,如加多了水的墨痕,只轻轻一点,就轻易渗透纸面,在背后变成泪。
九莉的心理描写,张爱玲常说一句话:“像被针扎了一下。”没有剧烈撕扯的疼痛,就是被扎了一下。你可以说这是张爱玲惯有的冷漠,但我心疼她,她总是被“扎了一下”,早已满身针孔了吧。
张爱玲的好友宋淇夫妇是《小团圆》的第一批读者。他们有两个担心:一是胡兰成会利用《小团圆》的出版而大占便宜,亦不会顾及到张爱玲的死活;二是九莉不是个讨喜的角色,自私、冷漠,读者的反感也许会波及张爱玲。但张爱玲还是这么写了。她坚持认为最好的材料是你最深知的材料。她宁愿不出版,也不想改动一个字。
幸运的是,我们读到了完整的、没有删改的《小团圆》。从1976年小说完成到2009年出版,历经30年之久。这期间,胡兰成去了,张爱玲去了,代理这部小说的宋淇夫妇也去了,所有他们曾经担心的问题都不存在了。时间是解决问题的高手,化一切于无形,谁还能争辩什么呢?
张爱玲大概早就明白这一点,她在小说里借九莉的口说,她没想通,好在她最大的本事是能够永远存为悬案,也许要到老才会触机顿悟。她相信只有那样的信念才靠得住,因为是自己体验到的,不是人云亦云。
生在那样一个显赫的家庭,却没有得到多少爱。母亲出国,父亲吸鸦片,整日无所事事。张爱玲和姑姑生活在一起,两个女人茕茕相对,既亲密又疏离,想来让人不寒而栗。也因此,小说里的九莉不相信任何人,包括三姑、母亲、同学,什么都要和他们分得一清二楚。尤其钱财,不会少给一毛,也绝不多占一分。她不落别人的“人情”,也不会送给别人“人情”。对与她无关的事,她更是漠然。一个极端的例子是,日本投降了,外面在放炮,消息传来,九莉翻了个身,继续睡了。
偏偏这样一个“冷酷”的人,遇到了邵之雍。她独对他有期待,想和这个男人白头到老。就算知道他有“二美”“三美”,她也尽量让自己理解——一个身处动荡中的人总要有些短暂的安慰。她甚至不顾自尊,千里迢迢去找他,让他做一个选择。但他到底不愿选择,说“牙齿好好的为什么要拔掉”。九莉觉得这是疯人的逻辑。她一直微笑着,不再问他,背地里却流眼泪,“那痛苦像火车一样轰隆轰隆一天到晚开着”。
其实以九莉的聪明,或许早就看透了,只是不想戳破。
小说第九章,张爱玲鲜有地用一整个章节描述一出戏。我以为这是《小团圆》的华彩。
戏的名字不知道,传统的才子佳人故事。公子和小姐私定终身,有了云雨之欢,公子去赶考,途中艳遇另一人家的小姐,一见再钟情。结局大团圆,公子考中,迎娶二美。
九莉坐在凳子上看戏,旁边不断有人嗤笑,说台上的戏子“怎么一个个都这么难看的”。台上演一段,底下就有人笑,“怎么一个个都这么难看的”。一句话重复了五次之多。
没有任何九莉的心理描写,但“怎么一个个都这么难看的”让人心悸。在邵之雍的理想世界里,三美团圆,九莉是其中一个。九莉为自己难堪:她居然想说服自己这是可以接受的。但现实是血淋淋的“难看”。
九莉看不下去了,站起来往外挤。她要的不是“大团圆”,而“小团圆”更是奢想。九莉终于明白了她和那些女人的区别。
“这些人都是数学上的一个点,只有地位,没有长度阔度。只有穿着臃肿的蓝布面大棉袍的九莉,她只有长度阔度厚度,没有地位。在这密点构成的虚线画面上,只有她这翠蓝的一大块,全是体积,狼犺的在一排排座位中间挤出去。”
这一段真是精彩。九莉“挤出去了”,对邵之雍的期待也幻灭了。
现实的情形是,1944年,张爱玲和胡兰成缔结婚约。胡兰成在婚书上写下“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但他没有给张爱玲一个安稳的现世。时局动荡,人心离散,他在逃亡中也不忘处处留情。最可笑又可气的是,他写信给张爱玲,常忍不住津津乐道于别的女子对他的爱,还责怪爱玲不会嫉妒。他真是将爱玲当作精神伴侣了。他用《聊斋志异》中的《香玉》打比方,说“香玉吾爱妻,绛雪吾腻友也”。他是想把张爱玲放在“腻友”的位置上。他欣赏张爱玲的绝世才华,享受他们的灵肉相通,同时也割舍不了世俗的爱。一个是仙境,一个是凡尘,他妄想上天入地,二者兼得。
張爱玲不是个传统的女子,但也向往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对胡兰成的那套逻辑很反感。后来在与友人的通信中以“无赖人”代称胡兰成,可见她的态度。
张爱玲24岁跟了胡兰成。最美的年龄。以她的桀骜、清高,却说遇见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直到尘埃里开出了花……
花还是萎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