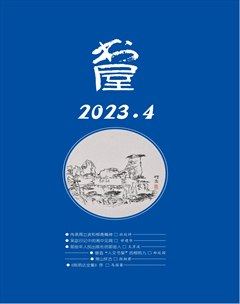湖南冬季的阴雨天气非常烦人,尤其是在1937年11月和12月间,吴宓日记中多是“雨不止,且寒甚”的记载。
先一天在武昌亦如此。11月18日晚上10时,好不容易挤上粤汉铁路南下火车,因卧车里面旅客太多,根本无法休息。直到翌日凌晨,乘客沿途散去,车中才稍觉宽敞舒适。“过洞庭、岳阳一带,巨浸茫茫,雾雨蔽空。既则山林湖沼,相衔而至,三楚风景,宓生平今初见也”。
当天下午一点半,车抵长沙站,到了大四方塘青年会,却被告知没有空房。恰好干事杨昌藩路过,见了大吃一惊,说:“这不是吴宓先生吗?我在您的诗集中见过您的照片。”原来他曾在北京师范大学读书,经常去同乡黎锦熙先生家,而黎之长女黎宪初(泽湘)是吴宓的学生,从她那儿了解到吴宓的一切。他不但读过《吴宓诗集》,而且读过吴宓批点徐志摩的《爱眉小札》,所以一见之下即认出本尊。他赶紧将吴宓和同来的清华生物系助教毛应斗安排到三楼最轩敞的贵宾房。可惜夜来风雨交加,房间高室悬空,风从玻璃窗缝隙而入,棉被又薄且小,吴宓“甚苦寒”。两天后,搬到圣经学院内清华外语系教授陈福田腾出的房间,与青年会的客舍恰成对比,“始得安眠焉”。
“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人与汉奸横行霸道,偌大的华北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国民政府教育部责令国立清华大学、国立北京大学与私立南开大学,紧急南迁至湖南组成长沙临时大学,三校大批教师与学生随之离开北平。清华外语系教授吴宓经过反复思考,不愿意做亡国奴,于10月27日中夜决计南行。在此之前,他力邀是年毕业的女弟子K(高棣华)同行,然而高棣华对于年龄大自己一轮并且离异的恩师并无爱心,因此一直举棋不定。直到11月3日晚上,高棣华才与其母商定,暂去已撤退到长沙的北平图书馆担任英文秘书,她的顶头上司是图书馆主任袁同礼(守和),两人很快陷入热恋之中,让远在南岳山中的吴宓听闻后心里很是不爽。同行的还有清华外语系两个女生,一个是北平辅仁大学校长陈垣之女陈慈,另一个张婉英,江苏淮阴人,生长于北京,先一年入读清华。到了长沙后,他将这三个姑娘暂时安排在圣经学院别院涵德女校宿舍,但基本上每天都带着她们仨在外面觅食。
吴宓离开北平是11月7日,行前因将别离客居多年的故都,心情变得极度凄凉黯然。在一家名叫凌风的理发店修容时,突然产生“宁可再来耶”之感,此后果真再也没有到过北平。
南渡到了星城长沙,吴宓逗留至12月5日,总计十七天之久。长沙临时大学租借的是浏阳门外韭菜园一号湖南圣经学院,因为房舍不够分配,文学院四个系另外安置到圣经学院的分校,位于离长沙尚有三百余里的南岳衡山。因为托运的行李未到,又找不到通勤车辆,加之生性疏朗旷达,好交各方朋友,“对长沙殊留恋”的吴宓,只好耐心等待时机。到了翌年1月间,长沙临大奉令西迁云南昆明,吴宓从南岳返回长沙,自1月23日至2月11日,再度居停二十天。前后加起来共计三十七天,湘中日记竟有两万来字之多。
到达长沙的当天下午,吴宓乘人力车至北门外下麻园岭二十二号,在清华大学办公处访晤同事沈履、潘光旦。而后到湘雅医院内省教育厅朱经农家,先见朱厅长,次见梅贻琦校长。吴宓向梅详细陈述了北平近况,以及清华园被日寇占据情形。梅贻琦只是颔首而听,神态似乎颇为冷落,吴宓明白这是对他迟迟没有到校的不满。
湘潭人胡元倓,字子靖,号耐庵,曾经担任湖南大学校长,是与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齐名的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清末拔贡出身的他,光绪二十八年(1902)入选湖南首批官费留日生,就读东京弘文学院速成师范科。翌年回国后,在长沙左文襄公祠创办明德学堂(今明德中学前身),不惜纡尊降贵,无惧冷嘲热讽,以“磨血办教育”的精神,实现教育报国的理想,在三湘四水传为佳话。吴宓当晚蹚着雨水泥浆前往泰安里明德学堂胡府探访这位前辈,但胡侄彦玮告诉他,胡翁已经休息,请他明早再来。第二天再去拜望,年已六十五岁的子靖先生,“虽病初起,精神犹强健”。念及十几年前,吴宓执教国立东南大学(后改中央大学,即今南京大学前身)西文系时,自任总编辑兼干事,与梅光迪、胡先骕、刘伯明、柳诒徵、马宗霍(衡阳人)等创办《学衡》杂志,“学衡杂志社”那块白底黑字的招牌就挂在吴宓寓所的门前。他们以极其鲜明的态度反对新文化运动,恪守“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宗旨,前后出刊七十九期,形成现代学术史上著名的“学衡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