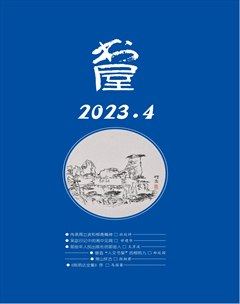一
1月23日,是我国英诗汉译界颇负盛名的杨德豫先生的忌日。2023年这一天,是他离开这个世界十周年纪念日。十年来,总想写点什么来纪念我这个师长般的朋友,但几次又把笔搁了下来。原因是担心自己这支秃笔,不能写出这位文化巨子于万一。
我自觉下放到大通湖的那段时光是本人此生的高光,其中之一,是有幸结识了这位杨德豫先生,并与他做了近四年的同事。更有幸与他同教中学语文,常常请益于他,那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
初次见到先生是在1969年元月,我们二分场各队冬修任务是疏通河坝至老河口那段河道。他是四队职工,我在一队接受再教育,为了提高效率,我们两队劳力都共同吃住于二队。晚上就同在二队的大会议室(其实就是一间大一号的茅屋)摊个地铺,只求把身子放倒就可以了。那场合的吵闹,可想而知。大声的叫喊、小青年的追打,夹杂着劣质的烟草味。却有一个中年人的地铺就摊在最中间,正心无旁骛地看一张《光明日报》。有人告诉我,那个看报的人就是“右派分子”江声,他是著名的翻译家。室内是一只大约二十五瓦的灯泡吊在中央,我想,先生把地铺摊在房中间,取的就是多一点灯光。从天黑到大约晚上十点,有三个小时左右,所有土胡子(当时农场职工自命的称呼)打闹过了,房内逐渐归于平静,工地负责人宣布熄灯睡觉。先生把报纸翻来覆去,好像把每个字都读了一遍,也才倒头睡觉。
此次冬修进行了十天左右,每天晚上,他都是如此。让我十分惊异的是,先生大隐隐于市、闹中取静的功夫和定力,没有十年八载乃至是童子功的修炼是很难达到的。
虽然有近十天的交集,但先生几乎不说话,显得有些难于接近,所以我与先生没有接触,就各回自己的队出工了。
可先生的相貌被我牢牢记住了:高高的鼻梁,两个眼窝有点下陷,直挺而高瘦的身材,步姿很有军人范儿。
二
后来,我把我现在的妻子处成了女朋友,她和先生是一个队的。于是,我到二分场四队的次数就多了一些。她们几个女孩就住在先生同一栋红砖墙但盖着稻草的房子。因为那是队上为单身汉盖的。我奇怪先生为什么没带家属来农场,她们让我上先生房子里去看看,说他的墙上贴着他的家史,但终觉有失礼貌,未敢贸然闯入。
显然她们是看过那家史的。从她们口中,我渐渐得知,先生是我国史学、文字学、金石学巨匠杨树达的哲嗣。杨树达先生一肚子中华传统文化,先后在湖南一师、湖大和北师大任教授,曾是毛泽东的老师。师生之间很有亦师亦友的情分,1920年还共同代表湖南民众北上北平参加“驱张运动”。直到1956年杨老先生病重,毛泽东写信慰问,并附上五百元慰问金。后到长沙,还亲临医院看望。另外,杨先生还告诉我,他老父亲评价一个人的文化功底,就只看他能背多少“四书五经”等古文。因这一点,文坛巨匠鲁迅先生都未能入他的法眼。有这等家学渊源,加之庭训颇严,因此,作为他的儿子,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不好都难。
先生曾就读于湖大、中央大学,遵父命学习历史专业。因实在不想在故纸堆里做书虫,竟不惜违抗父愿北上转入清华大学,拜在我国英语翻译泰斗冯至门下,学习英语相关专业。但大学未读完,1949年参军南下,担任过中南军区、广州军区报纸编辑。他的女友也是个热血大学生,是共产党的地下党员,被国民党特务用麻袋捆绑丢入长江。为纪念心上人的牺牲,他后来把自己的笔名写作江声。
三
我和先生有个共同的朋友叫白景高。老白和我一个队,满身文学细胞,“文革”前在《湖南文学》发表了好几篇小说,对先生也是恭敬有加。我不仅常从他口中得到先生的很多消息甚或是趣闻逸事,更通过他终于走近了先生。去到四队,总要到先生那儿报个到。我女友再三嘱咐我,闲聊莫要超过三分钟,不要耽误先生太多学习时间。那年月,我们尚无固定工作,又比他小了十多岁,面对渺茫的未来,都放弃了学习。先生的学习劲头又从何而来呢?这个问题我一直藏于心底,一天工休时间,我和老白在一起抽喇叭筒,便问老白。老白说,他呀,那是与生俱来的爱好,不让他看书,那会要他的命!
后来,我到场部“农业学大寨”展览馆助勤,之后,又去了河坝学校,到二分场四队去的机会就少了。不久,河坝学校的英语老师调离了,为顶这个缺,他也来到河坝学校。从二场四队到河坝学校,少说也有十公里地,他竟是用牛车把自己拖到学校,然后再把牛车送回队上去。据我所知,队上有好多他的青年粉丝,随便吆喝一声,那些青年人就会蜂拥而至,他那点行李还不够他们扛的。他就是这样一个人,生怕麻烦别人。一个学者型的人物到一个中学来任教,竟是自己赶着牛车而来。
匪夷所思的是,先生的英语课竟不被学生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