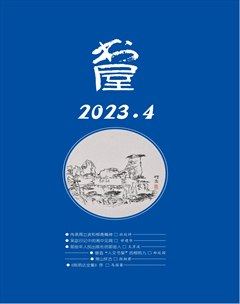一
十年前的那个午后,当我骑着单车穿过横跨渭河之上的蟠龙大桥,戴家湾便在桥北的蟠龙塬下。
有关民国时期戴家湾一带的情形,因时年仅二十五岁的苏秉琦先生曾参与北平研究院与陕西省政府合组的陕西考古会在斗鸡台一带的大规模考古发掘,故而留下了些许珍贵的记录。苏先生在《斗鸡台考古见闻录》一文中曾对戴家湾的经济与生活状况有如下记述:“本地人民的经济状况,都非常困窘……自然的原因:第一是耕地不足。例如陈宝祠所在的戴家湾,全村约六十户,耕地共不过四百亩。所以每户占地最多的不满五十亩,普通只三五亩。闹灾的时候,饿毙逃亡的,大约不下十分之三四,可以想见原来人口的稠密了。”
苏先生对关中一带因“鸦片繁荣”而带来的“陕西的黑化”深为慨叹和忧虑。他首先概述了当时这一情状的基本情形:“陕西的社会既如同烟鬼,所以当他犯了瘾以后的狼狈无力的情形,正好和我们前边所见的畸形的繁荣,是一个对比。”而后以戴家湾村为例,陈述了吸食鸦片所带来的两大“严重的恶果”:
第一是耗费的惊人。例如代家湾种烟二十六亩,一亩平均按收割五十两计算,共合一千三百两,可是代家湾的青年男子吸烟有瘾的就有三十多个,如果每人每天吃一钱,全年就需要一千多两。固然实际种的不只二十六亩,可是吸烟的更不只青年男子……
第二是劳动的不足。现在举几个实例,我们在斗鸡台所用的工人四五十名,是从附近的几十个村选拔出来的。因为凡有烟瘾的一概不用。所以代家湾虽然有五六十户,壮丁也当不下五六十人。可是淘汰的结果,只有二十多个是没烟瘾的,仅占总数的小半。
足见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陕西关中一带鸦片泛滥及其所引发的种种社会乱象是多么令人触目惊心。
绝然不同于民国时期那满目疮痍的民生惨象,现如今气势恢宏的行政中心综合体已经拔地而起,城市建设仍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戴家湾新建高层住宅间混合着村落中尚未拆迁完毕的老旧房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那个还没有高铁的年代,紧挨着戴家湾村半塬穿行而过的老陇海铁路显得异常繁忙——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营建陇海铁路时,出于对古迹陈宝祠的保护,在杨虎城将军和邵力子先生的主持下,铁路从陈宝祠下方、由其二人亲自题写碑额的“斗鸡台隧道”中穿行而过。斗鸡台即位于戴家湾村以北、戴家沟与刘家沟之间的一块台地。
苏秉琦先生在其撰写的著名考古学报告《斗鸡台沟东区墓葬》开篇便有如下记述:“乘陇海铁路火车,由西安至宝鸡,在未抵达目的地之前,经过最后一个小站,不远便看到一个隧道。在隧道洞口的上方,有一横额,曰‘斗鸡台’,即北平研究院曾经发掘过的遗址所在。因本院的发掘,事在铁路未通之前,据说,该隧道的穿凿,乃出于路局主管人保护古迹的美意,而非工程上的必需。因此,此一横额刻石,亦可说是本院在此发掘的一个纪念。”
1983年对陇海铁路进行电气化改造后,斗鸡台隧道便废弃了。现遗迹已全然湮没无闻,唯杨、邵所题写之两方“斗鸡台隧道”碑额至今仍保管于宝鸡市金台区文化馆内。
二
“陈宝”及“陈宝祠”史事,最早见于《史记》。所谓“陈宝”,一般或释义为“陈仓之宝”。东汉应劭曰:“时以宝瑞,作陈宝祠,在陈仓,故曰陈宝。”《史记集解》引汉魏时人苏林曰:“(若石)质似石,似肝。”《水经注》亦有“得若石焉,其色如肝”之语,从年代上看,陈宝“似肝”至少在苏林所处的汉魏之际已有流传,《水经注》著文史源或肇端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