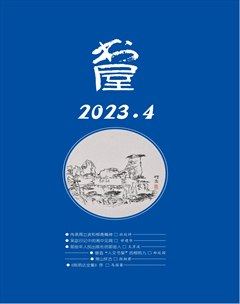我对柳鸣九的认知始于罗新璋。2004年暑假,罗新璋从北京寄我一信,里面附有柳鸣九手书的唐、宋诗人名句四种,且写有赠语。其一为:“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柳一村芳名,源出陆游诗《游山西村》,特录以赠。罗新璋。”其二为:“清溪清我心,水色异诸水。借问新安江,见底何如此。柳清兮芳名,源出李白诗《清溪行》,特录以赠。罗新璋。”其三为:“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柳相宜芳名,源出苏轼诗《饮湖上初晴后雨》,特录以赠。高慧勤。”其四为:“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柳觉晓芳名,源出孟浩然诗《春晓》,特录以赠。高慧勤。”
柳鸣九和罗新璋、高慧勤伉俪都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北京大学外语系同届同学,柳鸣九和罗新璋同班,学的是法语,高慧勤学的是日语。八十年代,罗、高跟随柳的步伐,陆续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由同学转而成同事,情谊由是更上层楼。罗新璋在信中告诉我,柳鸣九、朱虹伉俪拟赴美国探望四位孙女。柳鸣九嘱他将上面的内容以毛笔写成四张条幅,打算带到美国送给孙女们。罗新璋说,自己虽然被社科院的同事们誉为“书法家”,但只能用毛笔写写小字,大一点的字写不了,只好委托我这个远在长沙的朋友代劳。于是,我便花了好几天的工夫写就,连同柳鸣九的手书,一起打包邮寄给了罗新璋。
我原本以为柳鸣九只爱好法国文学,殊不料他对中国文学亦同样热衷。四个孙女,芳名全都由他取定,而且个个都发源于唐、宋两代的著名诗人,即是佐证。其实,他对中国文学的别有厚意完全在情理之中。“柳鸣九”中的“鸣九”二字不正是源于《诗经·小雅》中的《鹤鸣》吗?“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译成现代汉语,便是“幽幽沼泽仙鹤唳,鸣声响亮上云天”。柳鸣九的父亲曾挟厨艺而云游华夏,眼光甚为开阔,来往的友朋中肯定不乏文化人之辈。因此当儿子呱呱落地之时,父亲和友人们经过一番探究,“鸣九”两字便成了襁褓中幼童不同寻常的符号。孩提时代的柳鸣九时不时地和父亲身边的文化人打打交道,特别是在长沙市一中就读期间,著名记者严怪愚是他的语文老师,耳濡目染之下,中国文学的种子自然在他的心中深深地扎下了根,而且也为他青壮年时期乃至鲐背之年的笔墨耕耘奠定了格外坚实的基础。
后来的柳鸣九果然不负父亲的厚望。1953年7月,他脱颖而出,一飞冲天,以优异的高考成绩,从地处长沙清水塘的长沙市一中出发,过长江、跨黄河,直奔北京大学的未名湖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