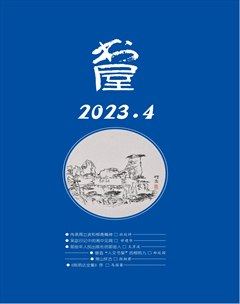当读者与作者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尤其是作者把读者只能意会无法言传之处用文字非常精准地表达了出来,那种阅读体验无比美妙。可能是多年来感觉到学界一些学者的作品比较缺乏“历史感”,或者觉得不少作品像“飘浮在高空中的一朵云”,距离普通人日常实际生活太远而缺乏“社会感”,即所谓的“不接地气”,当我近日阅读彭刚先生的著作《叙事的转向: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的考察》(以下简称《叙事的转向》)时,就产生了这样的共鸣,尤其是读到《历史理性与历史感》时,更是感到其中的道理甚合我意,与我长期的思考和感受合到一块儿了,并进一步启发了我对“社会感”和社会学研究的思考。
多年从事社会学研究使我有一个体会,社会学虽然说是以研究现代社会开启的学科,但从某种意义上看,何尝不是一种历史研究。费孝通先生总是说,从实求知,是从已经发生的社会事实里面分析总结出道理来。已经发生的“社会事实”在某种意义上也已经是我们的“历史”。不过,那些研究久远一些的社会问题或者现象,在一般社会学者眼里才是历史社会学的领域。历史和当下,甚至可以说“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位一体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缺乏“历史感”,也难以具备当下的“社会感”;缺乏对当下社会的体悟,同样难以具有敏锐的“历史感”。
作为学者,我们的作品,不论是著作还是文章,作为研究成果如果可以说是成功的研究,大概一定程度上就取决于作者的这种“历史感”和“社会感”,至少缺乏了它们一定不会是好作品。在这方面历史学与社会学是相通的。作为史学理论史研究者的彭刚先生在书中写道:“评判某一个特定的历史理解是否成功,当然有着多种因素和标准。在必须满足历史学在长期发展过程中所积累起来的对于史料运用的史家技艺的要求之外,有时候,我们甚至会仅仅因为某种历史理解所采用的史料或者其建构的历史世界违反了我们的经验常识而拒斥它。”接着引用伯克霍甫的话说:“一种历史的真实性,也可以根据它是否能够很好地与读者关于世界是如何运转的理解和经验相符合来加以判断。”这就要求史家对历史上社会(也可以说是映射着现实社会)的运转一定要有充分的领悟,否则就难以把历史文本呈现给符合读者体验的历史(社会)。作者这样把不同类型的学者进行比较,笔者深有同感:“科学史(比如数学史)上不乏不谙世事的天才,史学史上的史学大师却不能缺少‘世事洞明,人情练达’的健全理智。我们难以想象,毕生静坐书斋的历史学家,如果对于追逐权力的欲望完全陌生,却能够勾勒出具有说服力的政治史的图景……”何止是历史学研究需要“世事洞明,人情练达”,笔者从事的社会学研究同样不能只满足于“毕生静坐书斋”。社会学发展出了“田野调查”或者“实地调查”,但如果没有一定的“世事洞明,人情练达”基础,调查者到了田野也很可能成为被调查者愚弄的对象。在他们眼里,不懂人情世故的调查者就是“书呆子”,也许只是当面被恭敬而已。在对社会实际如何运转方面,社会学家和史家一样,必须“世事洞明,人情练达”,唯有如此,才能有“历史感”,或者笔者以社会学者的角度说,才能有“社会感”。
世界上看似矛盾的道理往往是辩证地统一在一起的。正如这样两则谚语所说:一则是“太阳之下无新事”,另一则是“历史绝不重复”。这恰恰正是历史“过去与现在、各种相似甚而看似无关或相反的历史现象之间,既有相通相同之处,又复有其相异相分的地方”。因此,作者说:“历史感的一个表征,就是对于这些异同的高度敏感和恰切把握。”由于这种同与异的辨析,“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切历史研究就都是一定程度上的比较研究,而对异同的敏感和辨析则是历史理性的重要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