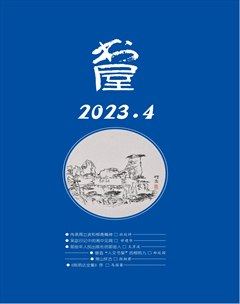黄郛(1880—1936),中国现代史上的重要人物,浙江绍兴人,原名绍麟,字膺白,日本东京振武学校毕业,1905年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时任沪军都督陈其美的参谋长兼第二师师长。1923年入阁,担任外交总长,9月改任教育总长。其时鲁迅在教育部任职,他就是鲁迅所说的“我所目睹的一打以上的总长之中”的一个,不过两个人之间没有什么个人的往来。1924年秋,黄郛参与策划了冯玉祥的政变密谋。10月24日政变成功,推翻了贿选总统曹锟,他即临时代理内阁总理,摄行总统职权。摄政内阁虽然存在的时间很短,却做了一件永载史册的大事:修改清室优待条件,永远废除皇帝尊号,清室应即日移出宫禁。把溥仪赶出了皇宫,完成了辛亥革命未竟之业,并宣布开放故宫为公共博物与图书展览场所。1927年5月国民革命军占领上海,黄郛被任命为首任上海特别市市长。1928年2月10日至6月8日任外交部长。1933年日本侵略华北的形势紧张,他被任命为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驻北平应对。1936年12月5日以肝癌去世。
《鲁迅全集》里两次说到黄郛。第一次是1919年3月15日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三号发表的《随感录五十四》(署名唐俟):
中国社会上的状态,简直是将几十世纪缩在一时:自油松片以至电灯,自独轮车以至飞机,自镖枪以至机关炮,自不许“妄谈法理”以至护法,自“食肉寝皮”的吃人思想以至人道主义,自迎尸拜蛇以至美育代宗教,都摩肩挨背的存在。
这许多事物挤在一处,正如我辈约了燧人氏以前的古人,拼开饭店一般,即使竭力调和,也只能煮个半熟;伙计们既不会同心,生意也自然不能兴旺——店铺总要倒闭。
黄郛氏做的《欧战之教训与中国之将来》中,有一段话,说得很透澈〔彻〕:
“七年以来,朝野有识之士,每腐心于政教之改良,不注意于习俗之转移;庸讵知旧染不去,新运不生:事理如此,无可勉强者也。外人之评我者,谓中国人有一种先天的保守性,即或迫于时势,各种制度有改革之必要時,而彼之所谓改革者,决不将旧日制度完全废止,乃在旧制度之上,更添加一层新制度。试览前清之兵制变迁史,可以知吾言之不谬焉。最初命八旗兵驻防各地,以充守备之任;及年月既久,旗兵已腐败不堪用,洪秀全起,不得已,征募湘淮两军以应急:从此旗兵绿营,并肩存在,遂变成二重兵制。甲午战后,知绿营兵力又不可恃,乃复编练新式军队:于是并前二者而变成三重兵制矣。今旗兵虽已消灭,而变面换形之绿营,依然存在,总是二重兵制也。从可知吾国人之无澈〔彻〕底改革能力,实属不可掩之事实。他若贺阳历新年者,复贺阴历新年;奉民国正朔者,仍存宣统年号。一察社会各方面,盖无往而非二重制。即今日政局之所以不宁,是非之所以无定者,简括言之,实亦不过一种‘二重思想’在其间作祟而已。”
此外如既许信仰自由,却又特别尊孔;既自命“胜朝遗老”,却又在民国拿钱;既说是应该革新,却又主张复古:四面八方几乎都是二三重以至多重的事物,每重又各各自相矛盾。一切人便都在这矛盾中间,互相抱怨着过活,谁也没有好处。
要想进步,要想太平,总得连根的拔去了“二重思想”。因为世界虽然不小,但彷徨的人种,是终竟寻不出位置的。
从《欧战之教训与中国之将来》这书名和鲁迅所引这短短的一段中,可以看出作者黄郛的忧国之心和他对国情的深刻思考,鲁迅是完全赞同他这意见的。
十五年之后,鲁迅又一次说到黄郛了。那是1933年5月17日鲁迅写的一篇杂文《保留》。文章开头就说:“这几天的报章告诉我们:新任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黄郛的专车一到天津,即有十七岁的青年刘庚生掷一炸弹,犯人当场捕获,据供系受日人指使,遂于次日绑赴新站外枭首示众云。”
鲁迅看了报纸的报道,立刻写了这篇杂文。他显然是同情投弹者这一方的。杂文的结尾说:
我希望我们将加给他的罪名暂时保留,再来看一看事实,这事实不必待至三年,也不必待至五十年,在那挂着的头颅还未烂掉之前,就要明白了:谁是卖国者。
从我们的儿童和少年的头颅上,洗去喷来的狗血罢!
这话的潜台词就是:投弹者不是卖国者,黄郛才是卖国者。
不过,依我说,这个投弹者当然不是受日人指使的汉奸,不是像张敬尧、白坚武那些日本人重金收买的汉奸那样的人。当时的清议多是主张对日强硬,“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不能容忍委曲求全,认为委曲求全、前往谈判的就是卖国者。
日本1931年9月18日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我东北三省。随后成立伪满洲国。1933年更加紧了侵略步伐。当时中日关系的紧张、华北的危急,就在收了这篇《保留》的杂文集《伪自由书》里也有不少反映。如《崇实》一篇,就是议论1933年1月3日,日本侵占山海关后,国民党中央常务会议于1月17日决定将故宫博物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等收藏的古物分批从北平运至南京、上海,以及教育部电令北平各大学“据各报载榆关告紧之际,北平各大学中颇有逃考及提前放假等情……查大学生为国民中坚分子,讵容妄自惊扰,败坏校规;学校当局迄无呈报,迹近宽纵,亦属非是”这两件事。《对于战争的祈祷》一篇,是从1933年2月,日本侵略军继攻陷山海关后又进攻热河,于3月4日攻占热河省会承德这件事讲起的。在日本侵略日益加紧,北平、天津危在旦夕的情况下,黄郛才被任命为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赴北平向日方接洽停战的。他当时接受这项使命是什么心情,在他北上途经上海的时候,和上海《大晚报》总主笔曾虚白的谈话中说得很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