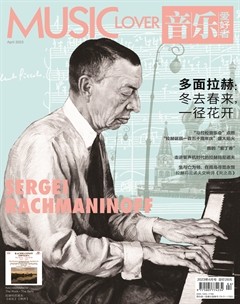哈萨克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由古代乌苏、突厥、契丹的一部分和后来蒙古人的一部分长期结合发展而成。我国境内的哈萨克族生活在毗邻哈萨克斯坦、蒙古国的西北地区,处于东连中原、西接欧亚腹地的中西文化交汇地带,主要分布在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的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阿勒泰和塔城三个地区以及昌吉回族自治州的木垒哈萨克自治县等地区,在甘肃南部也有少部分居住。
哈萨克族多从事畜牧业生产,千百年来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他们的聚居区有美丽富饶的盆地绿洲、绿草如茵的草原平川、风景如画的湖泊河流。天山北麓的伊犁河谷土地肥沃、水草丰盛,具有“塞外江南”之称。哈萨克族是一个能歌善咏的民族,谚语“歌和马是哈萨克族人一对翅膀”形象地说明了民歌是哈萨克族人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亲密伴侣”。
哈萨克族的文学和艺术非常发达,拥有丰富的品种和形式,其中民歌包括牧歌、颂歌、情歌、婚礼歌、挽歌、宗教歌等,演唱形式可分為弹唱、独唱、对唱等。哈萨克族民歌的旋律有着鲜明的民族特色和丰富的艺术表现力,这与他们的生存环境、生活习俗和语言特点息息相关、密不可分。勤劳智慧的哈萨克族人民创造出了别具一格的民歌,伴随着民族和历史的发展源源流淌。
旋律形态特点
哈萨克族作为游牧民族,随四季转场,长年居住在草原、森林。毡房与毡房、户与户之间的交流以及人与人的对话常常以呼唤开始,因此带有呼唤性的音调在哈萨克族民歌中最具特色。
呼唤性音调通常用四度或五度的音程关系以不同的形态出现在曲首,还可以发展为六度或八度的音程关系,以不同的曲调变体出现在作品内部。比如《燕子》的第一小节就是呼唤性音调,主音到属音的上五度进行出现在句首;副歌部分“啊”同样是属音到主音的进行,延续了歌曲的核心音调。《夜莺与百灵》则与之不同,其第三小节也是呼唤性音调,采用属音到主音的进行,在句首出现;副歌部分是主音到六级音的进行,随后以属音到主音收尾。

在哈萨克族民歌中还存在这样一种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歌曲开头第一句的句尾经常在调式主音的高八度上扬起,而结束终止却在调式主音的低八度上落下,形成一种对答、呼应的效果。作品《我的恋人》便是如此,该曲建立在F小调上,包括两个乐句。作品上句的第二小节为呼唤性音调,在高八度主音上扬起,而下句句尾第五小节则停在低八度主音上,形成了高起低落的现象。
长音拖腔是哈萨克族民歌的又一特点,这种特点在弹唱中尤为突出。例如在以冬不拉伴奏的歌曲中,凡演唱到长音拖腔时,冬不拉急促的弹奏就如鼓点般密集,衬托着演唱者的声音,把演唱者内心的情感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似乎不拖长音便不能尽情表达情感一样。《百灵鸟》为降A调,四句体乐段,第一句和第二句的句尾都有一个拖腔,第三句的句首、第四句句尾也有拖腔。衬词“啊”无限延长,这里往往需要演唱者自由发挥。
哈萨克族民歌旋律发展的主要手法是模进。它使歌曲的核心素材在不同高度上严格或变化出现,使旋律的主题十分鲜明,同时也成为扩展音乐结构规模的便捷手段,而且使民歌的调性有了新的变化,丰富了旋律,使人耳目一新。
歌曲《真心爱恋》的第二句就是在第一句的基础上做二度模进,第三句在第二句的基础上做二度模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