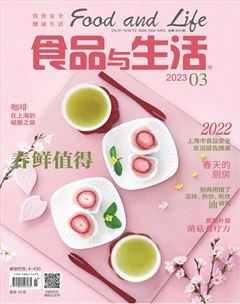25岁以后,我开始吃笋

儿时写文章用“雨后春笋”,虽知其比喻 义,却从未认真想过雨后的笋如何生长。我 人生的前 25 年不曾见过笋,可供人食用也 不过诗词中所见,只晓得那是熊猫的菜。
第一次吃笋是在合肥春意正浓之时,还 能记起街道名称,是一个冠以“天目山”名 号的餐馆,请饭的人,席间的客,一只古朴 的老鸭汤煲,香气婀娜,时光袅袅,都还依 稀在目。北方人不懂鸭子的好,鸭子做汤堪 称惊世骇俗,对当时的我来说也算见了世面。 此事倒是令我生出小小感悟 :阅历里常有盲 区,是因为主观的看不见,看不见的时候也 莫固执于鸭子不可能炖汤,世界那么大,眼 睛不过是个井口。
老鸭首先要“土”,其次要老,加上烹制 得法,湯汁才澄澈鲜美,肉质酥烂且略带韧 性。这鸭子能留存我记忆 20 余年,更在于 老鸭汤的搭档——笋。笋修长,整条呈锥形, 手指粗细,从汤里捞出,白净细嫩,身段柔软, 像练过瑜伽的样子。虽为配角,于一锅醇厚 的汤汁中脱颖而出,搛在筷子间,一个清纯 高雅的亮相,让我这来自北地的人暗自赞叹 一番。

登录后获取阅读权限
去登录
本文刊登于《食品与生活》2023年3期
龙源期刊网正版版权
更多文章来自

订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