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这里的路多得很。有一条是通向康脱拉的,另一条是由那边来的,还有一条是直接通向山区的。从这里看到的这条路我倒不知道是通向什么地方的。”说完,她用手指给我指了指屋顶上的那个窟窿,就在天花板破了的那个地方。
——胡安·鲁尔福《佩德罗·巴拉莫》
一
多年以后,当布朗 · 迈克披着风雪在公园里散步时,总会不由自主地回忆起那段起重机轰鸣的岁月。此时公园一片洁白,人烟稀少,而在另一个时空的当下,这是一片嘈杂荒芜的工地。这边布朗 · 迈克抱着摄像机驻足在冻结的喷泉旁,聚焦。另一个时空的他同样举起了摄像机,将镜头转向灵动活泼的喷泉。
老年的布朗 · 迈克终于意识到,所有人的生命不过是沧海一粟,终将被卷入瞬息万变的时代中,留下独一无二的代际印象。
他把手伸向天空,既无法捕捉消逝的秋风,亦阻挡不了来春的候鸟。盛夏蝉鸣不管不顾地响彻世间,轮回将把他湮没在时间长河里。
他能抓住的只有融化在镜片上的雪花。
二
人们不太记得大地曾经是什么样子,一个世纪好像一秒钟,世界天翻地覆。二十五世纪初,文明在战火里焚烧,硝烟和死人的鬼影无处不在。重建的工程拔地而起,日夜不息扰民清净。到处都是衣衫褴褛的孩童、邋里邋遢的男人、神经兮兮的女人。
幸存的人们经常放下手中的活,抬头望天,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切充满迷惘。疾病杀死昔日荣华,争夺资源的战争接踵而来,世界是个万花筒。
“孩子们总是一阵风来,一阵风去!”
塔瑞尔太太对着布朗 · 迈克先生喋喋不休,后者胡子拉碴,戴金边眼镜,正认真地记录中年妇女的话。两人旁边还蹲着一个不停用脏衣服擤鼻涕的小男孩。离三人不远处是一片坑坑洼洼的土地,上面星罗棋布堆放着一座座石子、沙子、砖头山。戴安全帽的工人驾驶工程车来回穿梭,施工噪音几乎把中年妇女的声音淹没。
“我年轻的时候,社会才不是这个样子。在我读大学那会儿,小孩子不会没人管教、到处撒野。他们要上很多补习班,好好学习,拿一个好成绩,找到好工作,生个好小孩……不准用衣服擦鼻涕,天哪,我要晕过去了!”
塔瑞尔太太裹了一条染有五颜六色菜汁、油渍甚至还有点发霉的围裙,头发随意地扎着。厚厚的茧子长年累月地在她的手掌里扎根生长,开出龟裂的花。她狠狠扯了一下小男孩的衣服示意他站好,然后把手往围裙边上蹭了蹭。
“你们这些文化人没吃过战争的苦,不然我也会和你们一样有一份像样的工作,而不是管小孩的吃喝拉撒。”塔瑞尔太太有些愤愤不平。
布朗 · 迈克下意识摸了摸他左胸前的口袋,那里夹有一支黑色钢笔,笔帽上若隐若现地刻着褪色的字迹:Glory(荣耀)。
那是战争发生之前的物件了。Glory公司作为文具巨头,每年都盈利滿贯。能够拥有一支Glory钢笔,是文化人的幸运。而战争发生以后,经济衰竭,市面上大部分股票暴跌,Glory公司也处于一蹶不振的状态。
和大部分人一样,布朗 · 迈克挣扎在生存的边缘,他失去了原本雷打不动的游戏公司文案工作,只能零零碎碎做些文字副业,变得有些萎靡不振。不幸中的万幸,一家杂志社正在面向社会征集与时代变化有关的非虚构文学,稿酬不菲,布朗 · 迈克自认为文字功底较好,便着手搜集写作素材。这是他第一次进行非虚构创作。
十分钟前,他从家里出发,到处走走,便遇上了邻居塔瑞尔太太。这位妇人的孩子趁她不注意时,偷偷跑到工地玩沙子,最终被严厉地批评了一通。借此,塔瑞尔太太倒了一通苦水。她不断追忆战争发生前的光辉岁月,世界井井有条地运行着。
“小伙子,世界变了,你知道吧?他们那群人不愿说,但我告诉你——”塔瑞尔太太压低嗓门,“以前是非常和谐的。但你如果说的话,大家不都会沉浸在过去吗?然后就没人收拾这些烂摊子了,就比如我家那个。”她无可奈何地摇摇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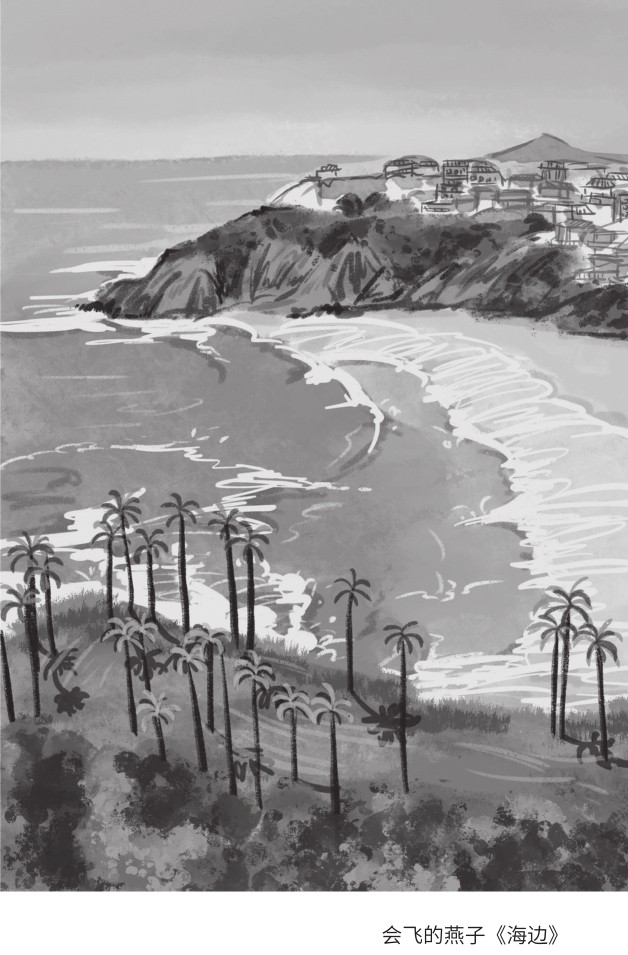
从塔瑞尔太太的口中,布朗 · 迈克得知她的先生就属于对过往闭口不言的那一类人。回忆使人沉沦,人们踏上现实的断头台,每回一次头就要被无形的刽子手砍去一次脑袋。塔瑞尔先生拒绝回头,拒绝被砍去脑袋。他是一家公司的小职员,每天只会雷打不动地上下班,表情沉闷,在家里也很少说话,成为一台到点了就自动出现在餐桌旁嗷嗷待哺的取款机。塔瑞尔太太不得不操劳家里一切大小事务,青春女学生变成了啰唆老太婆。
“幸亏你今天碰上了我!我和你说,你们这些年轻人啊,没见过战争以前的情况,实在是太可怜了。那个时候我读大学……”
布朗 · 迈克把站立重心从一只脚换到另一只脚,感到有些无奈。塔瑞尔太太已经滔滔不绝地讲了一个小时,但她总是停留在对最表面的物件的抱怨上:衰落的Glory钢笔、价格暴跌的乳制品、忽然满屏雪花的电视机……当然,谁能说物件的变迁不是时代的变迁呢?不过布朗 · 迈克始终希望她能说些一针见血的观点,能够为自己的文章嵌入核心。他渴望通过语言把握时代的脉动,却始终找不到。
工地上的嘈杂阴魂不散,吵得布朗 · 迈克感到越来越烦躁。不久他便找了个托词和塔瑞尔太太匆匆告别,脑子里一直在思索着当事人的言论。碎片、零散、聒噪,这是他应该写出的时代面貌吗?不知道。布朗 · 迈克疲惫地走在回家的路上,形如一只被时间蒸煮透了的虾。
布朗 · 迈克感觉自己的信心略受打击,沮丧地回到家。落日把平房的影子拉得很长。道路两旁总是有各种各样的沙堆、石堆,远远望去像一座座坟墓。世界金灿灿的,几个孩子快乐地玩跳绳。布朗 · 迈克关上门,把一切暂时隔绝在身后。一天又这么结束了。
三
一个戴安全帽的人双手叉腰站在一辆铲车旁,车里的人正探出头和他说话。说了大约五分钟,铲车便开走了。留下的人转过身来,注意到五分钟前就有个陌生青年坐在工地外边的一个板凳上,似乎一直在托腮思考着什么。青年三十岁左右,胡子有一段时间没刮了,眼神呆滞,头发微乱,一副阁楼里的艺术家模样。
戴安全帽的男人朝坐在板凳上的男人走了过去。
布朗 · 迈克抬了抬眼神。
“看啥?”戴安全帽的男人问。
“看你们施工。”布朗 · 迈克说。
“不是,施工又不是拍电视剧,有什么好看的?”
“这叫文学的写生。”
这片荒地离布朗 · 迈克的家很近,因为人迹罕至并且空曠,所以他经常来这里放空自己。他搬过一次家,上一次是在一座闹市,周围挤满了塔瑞尔一家那样的人。写不出合适的文案时,他会搬出自己的板凳,坐在阁楼顶上思考。现在思考的习惯还在,只是没了工作。
戴安全帽的男人肤色黝黑,帽檐压得有些低,在他的额头前投下一片阴影。这人身穿泛黄的工地服装,左手拿一盒廉价牛奶,右手提一个纸袋,在布朗 · 迈克的右边盘腿坐下,摘下安全帽放在地上,露出焦炭色的头发。他打开纸袋,里面是尚有热气的热狗。
布朗 · 迈克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看。
戴安全帽的男人一边大口吃着热狗,一边观察工地。先前那辆铲车试图从两座石子小丘中间开过去,但轮胎似乎压到了石头,开得有些艰难。他小声嘀咕了句,一转头又发现布朗 · 迈克在往这边看。
那人歪了歪头,感到有些疑惑,不过仍然一言不发地吃热狗。布朗 · 迈克和他打声招呼,试图找个话题:
“这里是要盖什么吗?”
“公园。”那人吐出一个词。
“我们国家战后基础设施恢复得很快。”布朗 · 迈克盯着那一辆黄色铲车,它艰难地从石子堆中间挤过去,铲着泥土行驶到指定地方堆放下来。一个星期以前和塔瑞尔太太在这里相遇时,背景还是一片坑坑洼洼的空地。此时地面上已经铺了水泥板砖,还有一些游乐设施的雏形。
戴安全帽的男人说:“哦,这就是我们的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