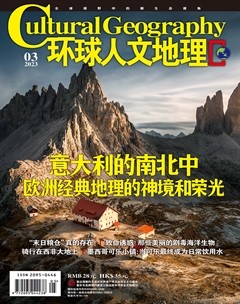重庆人管涮火锅不叫涮,叫烫火锅。 1980年以前,重庆市面上几乎看不到几家火锅馆。重庆的冬天,温度并不低,很少在零度以下,但体感很冷,那种湿冷,往骨头缝里钻。重庆人就在屋子里点一只煤油炉或者蜂窝煤炉子,上面置一口铁锅,先是用菜籽油和郫县豆瓣酱、干辣椒、山奈、八角、草果、老姜、白糖一起炒,炒得香气四溢,再倒进大半锅水。红滚滚的汤水熬上一阵,佐料的味都熬进汤里,再从碗橱里摸出一碗牛油来。牛油储存时间一般有点长,板结在碗里,异常坚硬,得用尖刀,费劲撬松,取两块,扔进锅里,等着牛油彻底化了,一股散发着牛油香气的火锅锅底就算完成了。
重庆人烫火锅的食材,荤菜以猪、牛下水为主,再加些猪五花肉片和牛肉片就算丰富了,素菜一般喜用包菜、小葱、蒜苗、黄豆芽、平菇、牛皮豆腐干和红苕粉。
那时候,重庆一入冬,亲朋好友聚会,招待外地客人,在家里烫一顿火锅算是标配。当时居家条件都不太好,天氣阴冷,房屋密闭性差,处处透风,没有空调,更没有地暖,做一桌菜,还没开席,就凉了。烫火锅隆重而爽利,既暖身又尽兴。如果招待贵客,食材上就会加些鳝鱼片、青蛙、午餐肉之类的门面菜。
那时候,菜市场专门有卖鳝鱼的,现卖现杀,把内脏骨头剔干净,划成片状,带着浓稠的鳝鱼血,重庆人把这种鳝鱼片叫“血片”。蛙是乡下农民夜里下水田逮的,用麻线绑成串,装在一只竹编的笆篓里,大清早就背到农贸市场来卖。那时候重庆男人都会打整蛙(重庆方言,意为收拾青蛙),用小刀在蛙的后颈皮上划一道口,顺着就把蛙皮剥下来,再把内脏一挤,最后剩一身雪白的蛙肉,外带腰间飘一绺黄色的蛙油。午餐肉,数上海梅林牌午餐肉最受欢迎,从铁皮罐头盒倒出来,切成一片片小方块。即使物质极度匮乏,重庆人待客备的菜,也总大大超出客人的胃容量。一场火锅烫下来,荤菜可能所剩无几,素菜总要剩几盆。
那时候,国人食物普遍少油,摄入脂肪量严重欠缺。重庆的地貌高低起伏,公交设施匮乏,重庆人每天几万步脚程算是稀疏平常,消耗极大,大都长得精瘦,谁长得略胖,大家都夸他身体好、墩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