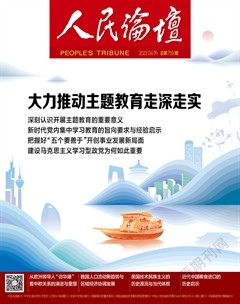【关键词】微腐败 反腐倡廉 基层治理
【中图分类号】D262.6
【文献标识码】A

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提出“微腐败”概念,并强调“微腐败”也可能成为“大祸害”。2017年1月,十八届中央纪委七次全会对“严肃查处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进行了工作部署,显示了党治理“微腐败”的强烈决心。2023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强调:“要坚持内容上全涵盖、对象上全覆盖、责任上全链条、制度上全贯通,进一步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使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更好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在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过程中,强化“微腐败”有效治理成为了反腐倡廉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
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败斗争取得了显著成效、积累了重要经验。即便如此,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特别是基层腐败问题突出。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数据显示,2022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处分省部级干部53人,厅局级干部2450人,县处级干部2.1万人,乡科级干部7.4万人,一般干部8.3万人,农村、企业等其他人员41.3万人。有效治理“微腐败”,坚持反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成为当前反腐败斗争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工作。为了有效治理“微腐败”,深入了解和梳理“微腐败”现象的易发领域、易发主体以及诱发原因至关重要。
“微腐败”具有“小”“多”和公众对其态度模糊的特点,常见于群众自治组织、拥有公共资源的单位和掌握行政权力的乡镇基层机关之中
“微腐败”现象涉及社会生产生活中的各个领域,表现出“小”(乱用公权力行为的恶劣影响不大)、“多”(乱用公权力的行为较为普遍)和公众对其态度模糊(公众既能容忍“微腐败”,又憎恨“微腐败”)等特点。就发生频率来看,“微腐败”现象常见于群众自治组织、拥有公共资源的单位和掌握行政权力的乡镇基层机关之中。
首先是基层群众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是我国村(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微腐败”现象不仅仅滋生于村民委员会,也常见于居民委员会之中。乡村“微腐败”多见于农村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公职人员凭借手中的权力,为自己或他人谋取私利。中国农村是典型的人情、面子和关系型社会,农村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中的工作人员不仅仅是乡镇党政机关在农村的“代理人”,也是村民选举出来的代表。与此同时,村民委员会还掌握着集体财产,在补贴发放、低保办理、房屋拆迁和土地征收等工作中扮演着重要作用,除了要落实具体任务,还要担负起监管职能。一旦村两委班子成员无法有效规制自身行为,以权谋私,村民委员会将会成为少数人谋取利益的私器。我国农村基于血缘和地缘因素极易形成“差序格局”,以自己为中心,形成错综复杂的社会网络,为优亲厚友、索贿受贿提供土壤。“家中有人好办事”“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成为了一些农村地区的真实写照,这些不正之风不仅没有随着社会进步而被摈弃,反而在一些地方“盛行”。
相对于农村,城市社区层面的“微腐败”现象也是不可忽视的。城市“微腐败”主要存在于房屋拆迁、基础设施改造升级和公共服务保障等具体领域。比如,在房屋拆迁领域,随着城市化进程和棚户区改造工程的推进,社区居民委员会在协助政府相关部门开展拆迁补助工作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由于在各项具体工作中掌握了较大话语权,一些社区居民委员会成为了以权谋私的主要载体。更为重要的是,“抱团腐败”成为了“微腐败”的重要表现形式,由于工作关系,有关人员容易形成共同利益链,出现腐败“群体作战”。
其次是拥有公共资源的单位。掌握社会公共资源分配的单位出现“微腐败”的可能性也比较大,主要是由于他们具有排他性的资源分配权力,比如矿山、林业、水土,以及医疗、卫生、健康等民生领域容易成为“微腐败”的温床。涉及民生领域的“微腐败”现象成为了腐败爆发的重灾区,且尚未得到有效根治。虽然发生在诸如惠农资金、新农村建设、教育与医疗、生态环境保护等领域的“微腐败”涉及金额不大,但直接侵害了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
民生领域的“微腐败”主要是“雁过拔毛”的小贪小腐,表现形式也多种多样。一是少数公职人员违法搭乘专项拨款的“顺风车”,违规骗取民生“奶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