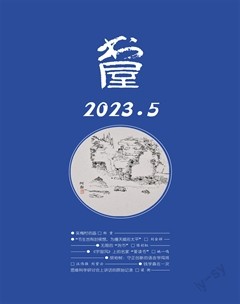思想者或者作家,哲学或者文学,有一个别样的衡量高下的尺度,那便是对于女性的态度。
鲁迅的女性观是鲁迅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鲁迅对一个一个女性的具体态度则最为生动地体现了他的女性观。贯穿鲁迅女性观始终的,只有两个字:解放。这是双重的解放,从专制奴役中的解放与从男权重轭下的解放。
一
获得解放最直接的途径当然是革命,对于挺身而出的女革命者,鲁迅总是怀着一种对于行先者的格外的尊敬、佩服、理解与爱戴。不是居高临下地施以光泽,而是心悦诚服地发现她们可以照亮黑暗的光泽,并满怀热爱地理解、体贴,甚至还有一些仰望与崇敬。
革命者秋瑾与鲁迅是绍兴同乡,他们早年先后参加了光复会,又都是辛亥革命的拥护者与参与者,这便有了血脉的相通。但是他们又有着重大的差异与分歧,一个是激烈的行动的革命者,一个是温情的将译介与创作作为工具的思想启蒙者。虽然秋瑾与鲁迅有过共同留学日本的经历,在1905年年末共同参加中国留学生抗议日本政府颁发《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的行动时却有过重大的分歧:秋瑾主张留日学生全部罢课、退学、回国;鲁迅则主张短期罢课,并反对退学回国。
但是这些差异与分歧丝毫不能减弱鲁迅对秋瑾的怀念与钦佩。1907年7月15日凌晨被就要灭亡的清政府斩首于绍兴轩亭口丁字街头,从那时起,秋瑾就一再地被鲁迅提起与纪念着,尤其在人们早已将烈士遗忘、复古复旧复辟的时候。十八年后的1925年12月29日,鲁迅写下论战长文《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第四章是《论不“打落水狗”是误人子弟的》,沉痛地说:“秋瑾女士,就是死于告密的,革命后暂时称为‘女侠’,现在是不大听见有人提起了。”一句“现在是不大听见有人提起了”,是对于烈士落寞与寂寥的体察与惋惜。这种体察与惋惜一直在鲁迅的心上放着,再过了九年的1934年12月11日写下的《病后杂谈》,重新记起秋瑾临刑前的那句“秋雨秋风愁杀人”;紧接着又在《病后杂谈之余》中,痛切地说到人们的忘却:“轩亭口离绍兴中学并不远,就是秋瑾小姐就义之处,他们常走,然而忘却了。”
最能表达鲁迅对秋瑾心情的,还是写于1919年4月的小说《药》。尽管愚昧与黑暗笼罩着中国,秋瑾还是慷慨地抛洒了一腔热血,哪怕这一腔的热血只能换回冷的“人血馒头”。在鲁迅那里,一个夏瑜(秋瑾)代表了许多辛亥革命的牺牲者,而忘掉这些牺牲者则不仅是倒退,甚或竟是一种背叛。所以取名夏瑜,固然可以解释为“夏”“秋”相对,“瑜”“瑾”互映,或者“夏瑜”谐音“夏逾”,而有“秋近(瑾)”之义——但我还是觉得,在鲁迅的心上,夏瑜(秋瑾)便是一块华夏之美玉,无比珍贵。
刘和珍则是民国遇害的新女性。《记念刘和珍君》让我们永远地记住了她。这是一座爱与憎的丰碑,将中国最早觉醒又最富牺牲精神的新女性形象恒久地保鲜在中国的大地上,同时也将屠杀者的残暴与罪孽永久地铭刻在历史的账簿里。而那个牺牲在北洋军阀枪弹与刀棍之下的只有二十二岁的刘和珍,一个“始终微笑的和蔼的”、温和而美润的女子,也便因为鲁迅的爱惜与崇敬而永存在这个国度里。这是熔岩般的文字,与痛惜国人忘却秋瑾一样,依然是“忘却的救主快要降临了罢,我正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正如多年后写下的《为了忘却的记念》,不是为了忘却,竟是为了永留——就是要用文字阻断遗忘并为这个民族敲响警钟。
鲁迅用“勇毅”来表达对刘和珍、张静淑、杨德群这批新女性的赞颂:“当三个女子从容地转辗于文明人所发明的枪弹的攒射中的时候,这是怎样的一个惊心动魂的伟大呵……我目睹中国女子的办事,是始于去年的,虽然是少数,但看那干练坚决,百折不回的气概,曾经屡次为之感叹。至于这一回在弹雨中互相救助,虽殒身不恤的事实,则更足为中国女子的勇毅,虽遭阴谋秘计,压抑至数千年,而终于没有消亡的明证了。”压抑数千年,最早醒来并试图反抗者却横遭杀戮,这不仅是女子的悲哀,更是旧中国的悲哀。那些日子,虽然有着许广平的亲近,却也不能稍稍减轻他的悲愤,不睡,不吃,在“老虎尾巴”与逃匿的日子里,抛开被逮被杀的危险,鲁迅不顾一切地与“刘和珍们”站在一起,连续写下七篇关于“三一八”惨案的血泪控诉。
“这不是一件事的结束,是一件事的开头。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写于1926年3月18日的《无花的蔷薇之二》的末了,鲁迅专门记下这样一句:“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我们从此可以一再地看到这样“最黑暗的一天”与刘和珍温和的笑容。好在那时的鲁迅并不孤单,周作人、林语堂、朱自清、蒋梦麟、王世杰、闻一多、梁启超、许仕廉、高一涵、杨振声、凌叔华等都与鲁迅一起,各自发声发文写歌声讨与谴责;而《语丝》《国民新报》《世界日报》《清华周刊》《晨报》《现代评论》《京报》等报刊,也一起站在声讨与谴责的立场上刊登大量的图片与文字。
二
鲁迅逝世的消息,丁玲是在前往延安的途中得悉的。她悲痛之中立即给许广平发去一封唁函,這样表达她的内心:“无限的难过汹涌在我心头……我两次到上海,均万分想同他见一次,但为了环境的不许可,只能让我悬想他的病躯,和他扶病力作的不屈的精神!……这哀恸真是属于我们大众的,我们只有拼命努力来纪念着这世界上一颗殒〔陨〕落了的巨星,是中国最光荣的一颗巨星!”
唁函署名“耀高丘”,来自鲁迅的旧体诗《悼丁君》中“可怜无女耀高丘”一句。1933年5月14日,丁玲在上海虹口昆山花园路7号寓所被国民党反动派秘密逮捕,6月便有丁玲被杀的传言散布开来。传言鲁迅是信的,“三一八”“四一二”以及柔石等五位青年作家的被害,革命者的血淡了又鲜。鲁迅的这首诗写于听到传言之后的6月28日,用一个“悼”字,与数月前写下的《为了忘却的记念》一样沉痛。丁玲被捕,鲁迅与杨铨、蔡元培等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同人一起奔走营救未果,才写下这首诗寄托一种疼惜、愤怒与反抗,还有隐隐的无奈。营救未果,营救者杨铨先已被国民党特务杀害,6月21日刚写下《悼杨铨》:“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1931年2月,鲁迅还写下悼念柔石的《无题》:“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鲁迅一生四次写下悼亡诗,除这三次外,最早是写于1912年的《哀范君三章》,悼念范爱农,“世味秋荼苦,人间直道穷”,“独沉清冽水,能否洗愁肠”,“大圜犹酩酊,微醉自沉沦”。四次悼亡,唯独《悼丁君》鲁迅主动寻找发表的园地,9月21日致曹聚仁信:“旧诗一首,不知可登《涛声》否?”9月30日果然刊登于《涛声》周刊。
写下这首诗的前后,鲁迅一直在密切地关注着丁玲的命运。《〈伪自由书〉后记》里有“五月十四日午后一时,还有了丁玲和潘梓年的失踪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