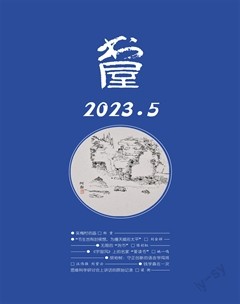检点《从大都到上都:在古道上重新发现中国》(以下简称《从大都到上都》)的作者罗新的经历,本科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硕士、博士则转入历史系,以后就主要从事历史学的研究。如此,此书称得上是文学专业与历史专业的奇妙结合,以文学的注重感性、长于描述冲淡了历史过于板正的一面,同时以史学的实证与考据功夫挽救了文学的虚飘,使整本书呈现出厚重而不失润泽的面目来。
作者是个妙人,读他的文字,时刻能感觉到他作为学者的矜持,虽然用徒步的方式行走,想努力跟路上遇到的各色人等打成一片,可事实上做不到。他一直端着身架没有放下来,将自己和人群的距离隔得很清楚,这与学生口中“罗老师刻意保持和学生的距离”的说法是一致的。与此同时,作者对同类人又保持了高度敏感,路上但凡遇到一个“谈吐不似一般村民”的人,都要追问人家是不是老师,罗老师对教师这个职业的忠诚度委实让人感动,也增加了资历尚浅的我的信心。但是,对少数同类人的认可,正可见出与多数人的隔膜,罗老师在本书的后记中将旅游者与旅行者进行了仔细区分:“旅行者不是来猎奇的,你短暂地(哪怕是浅浅地)融入你所经过的一切地方,你不是高高在上的游览者,你是背负行囊汗流浃背的过路人,你是需要而且一定会得到同情的远行客。”——显然他把自己归入旅行者的行列了。然而在我看来,他并没有真正成为旅行者,他做到了背负行囊汗流浃背,也获得了同情(吃饭住宿时常被减免费用),但始终保持着未必高高却一直在上的姿态。旅途中唯一一次真正忘情的时刻,是在瓦窑村看村民打升级:“我蹲在一个穿红上衣、戴珍珠项链的中年妇女背后,看她起牌、出牌,看得入迷,忘乎所以,竟然支起招来。从我的支招中获利的这一位似乎看出我的牌技更高,或瘾头更大,而且出于礼貌,把牌交给我,说:‘你来打,你来打。’我猛然意识到我并不是在三十年前的北大32楼,赶紧推辞:‘你打你打,我马上要走了。’”——读者看到这里,大概不免莞尔一笑,这才是教授与村民平等、罕见的得大自在的时候。
作者的学院式知识分子做派不独表现在身份的矜持上,也包括近乎严苛的旅行计划。每天开始与停止行走的地点都是提前计划好的,绝少有变动,而且有板有眼。比如今天在甲地止步,但预定的旅馆在前面乙地,那就让旅馆的车来接,次日再坐车返回甲地重新开始行走,以此保证全程步行,一点也不偷工减料。严谨当然是好习惯,在缺少监督的情况下能做到不苟尤其难得,作者能取得那么多学术上的成就,与这种自律的习惯肯定是分不开的。但事实上古人行旅,势必无法做到如此精确,他们会有走冤枉路的时候,有挨饿与投宿无着的时候,有流连山肴野蔌的时候,有醉酒迟起的时候,甚至有遭遇盗匪侵袭的时候。总之会有许多意外情况发生,不可能完全按计划来,保证走的每一步都不浪费。在这个意义上,计划的周全、执行的严格以及完成的顺利,并不一定完全值得赞美。“我没想到自己这么快就喝完了一瓶啤酒,王抒问要不要加一瓶,我没敢,怕喝得迷迷糊糊影响走路。”——看到类似的话,总不免有些替作者遗憾。按照作者所说,徒步是对主流的抵抗,但作者徒步的方式,却又有意无意地迎合了主流的标准,带有完成科研任务似的紧张感,这大概是生当此世的人很难摆脱的习性或曰宿命吧。
忘了在哪里看到过一句话,大意是年轻时读游记,喜欢漂亮的辞藻与修辞,待年纪大点,兴趣就变了,更愿意看路上遇见什么人,小酒馆里吃了什么饭,价钱如何,与人聊点什么话之类的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