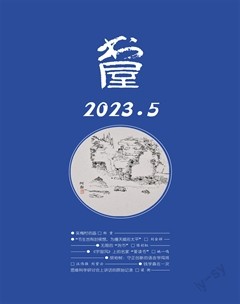按语:整理旧资料,发现一个记录本,是一次思维科学研讨会的笔记。这是钱学森同志亲自主持的一个小型会议。时间是1984年8月7日—11日,地点在北京北三环的远望楼宾馆,参加者共五十九人。这并不是什么官方会议,是因钱老热心这个题目,就召集平时聚在他周围的一些人开了这么一个会。
会议主要是钱学森同志讲话,讲他近几年对思维科学的一些思考。钱学森同志用了一整天作开场报告。他讲完后就坐在台下,连续几天像学生一样听大家发言。到会的人虽都是专家,但对别的学科都表现出学生式的谦虚。
会议的主要服务人员即主要承担会务的是张光鉴先生。他当时是太原一个军工厂的工程师,也是全国人大代表。因为同是军工口,他与钱老熟,钱就委托他跑腿。我当时是《光明日报》记者,驻山西记者站,与张熟悉。当时我们两个正热心研究“相似学”,我又正在写作章回体《数理化通俗演义》,书的最后一回专谈“相似论”。因为写了一篇论文“论相似”,张曾领我去办公室拜见过钱老,后来这篇文章发表在1984年8月的《光明日报》上。1985年1月我又在《山西师院学报》发了一篇《文章自然相似论》。因为这层关系他就把我拉进来参加会议。记者习惯,我全程做了详细笔录。
会议的一些主要参加者如钱学森、高士其、李泽厚、吴运铎、胡寄南等先生已经作古。时间过去了近四十年,好像还没有看到关于这次会议的公开材料,特将记录整理出来公布、存真,并纪念钱老等一批先行的思想者。当然,四十年来科学进步,谈话中的有些问题可能已发生变化,但其史料价值不减,学术在变,学者精神不变。如其他与会者手中还有相关资料,也请能相互补充印证。
原会议记录约一万五千字,受篇幅所限,这次只選取钱老的讲话和插话发表。
梁衡 2023年1月23日
这个会是学术性的,年轻力壮的(同志)组成会务组为大家服务。许多同志只在文章上见过,现在认识一下。
思维科学说新也不新,已研究很久了。我今天的发言不成体系,也不是学术报告,拉拉杂杂,耽误大家一天的时间。
对研究思维科学要有一个紧迫感,它比系统工程已晚了几年。1979年10月关于系统工程由国防工委支持开了个会。1980年11月成立了系统工程学会。我们已经晚了五年。去年10月9日中央领导同志提出新技术革命的对策问题,马洪主持开了两次对策讨论会。那么思维科学与新技术革命是否有关系?
人类社会的四种革命:1.认识客观世界的飞跃,叫科学革命。2.改造客观世界的飞跃,叫技术革命。3.这两种革命引起生产力发展,引起上层建筑的飞跃叫产业革命。(此处似应有一句:4.社会革命。——梁注)
人类社会已经有好几次(变化)了。(1)最早的是从自然界掠取食物到有了农业、牧业,引起了人类社会的变化。(2)奴隶社会生产力发展,出现了商品生产,进入封建社会。从这两次看产业革命引起制度变化,那么是否产业革命就必然引起社会革命?(3)但是第三次产业革命,十八世纪末的那一次,就是我们常说的工业革命,蒸汽机的出现,实际上是英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已经站稳了,是社会革命在前,产业革命在后。(4)第四次产业革命就是列宁说的工业变成世界化,标志着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社会制度没有变化。这说明产业革命和社会革命的关系不一定是产业革命必然引起社会革命,我国就是共产党先掌权才有产业革命。
这四种革命和思维科学有什么关系?国外讨论(按我的话说是第五次)产业革命的特点是什么?《红旗》1984年第十四期建议不要用“信息社会”这个词,而叫“信息社会化”,意思就是信息、知力(原文如此)要提到一个很高的水平。这个领域实际上与我们的思维科学很有关系。
什么是信息?文字信息和情报是一回事,我认为就是知识。人通过实践认识到的规律性的东西,是人类的精神财富。图书资料、档案、唱片录音都是精神财富,现在这些东西也要变成生产力。一方面要创造知识,一方面要用知识,这是我们的任务。
卡尔·波普尔创造了三个世界理论。人是“世界一”;客观世界是“世界二”;人创造的知识是“世界三”。奇怪的是他认为这个“世界三”是独立存在的。卡尔的这句话我赞成。我们想一想,假使现在打了一场核战争,把地面上的建筑财富、物质财富都打光,精神财富也打光了,我们要重建社会要一百万年,又要从猴子变人开始。但是如果只摧毁了物质财富,精神财富保存了下来,那么只要几十年就可以建成。这把知识的重要性说得很清楚。
什么是知识?一个是科学,但还有一个约束科学,必须是相互连起来的整体,不只是自然科学,还有社会科学。
知识还不止于科学,人还有很多知识只是经验,还没有上升到科学。如中医是不是科学,为什么总重视不起来?我想,关键中医不是现代科学,它只是经验,阴阳五行,现代科学解释不清楚。它是知识,不是科学,客气地说是经典意义的自然哲学。这是恩格斯的话,自然哲学,不是科学,它有猜想因素。但是这不是说它不重要。我们有许多知识就是经验,是精神财富。我们每人都有,但不是科学。这部分应包括到知识中去,可以叫“前科学”,是进入科学以前的人类的实践经验,这都和思维科学有关系。这个“前科学”量是很大的,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不是固定的东西,经常变化的。一部分“前科学”被条例化了,纳入到科学里,但“前科学”不会少,它又不断得到补充,人的实践不断认识无止境,这就联系到了思维科学。
人的思维就是人自己能控制的意识。人有许多下意识,不用大脑控制,这是人体科学部门的研究。我们思维科学研究人大脑控制的人的思维。一靠实践,二靠智力、知识。而且后者越来越重要,是实践的补充。所以人的思维是集体的,学术讨论更说明了这个。我国的学术讨论不兴旺。一个人讲完,其他人不说话。又一个人再讲,讲别的。再一个人讲,还是这样。外国不是这样,所以我们怀疑学术讨论是不是西方特有的东西?去年8月26日《光明日报》第三版上有一篇谈古代书院的“讲会”制。我一看高兴了,学术讨论的老祖宗还在中国。他讲到了朱熹当年的讲会、辩论,师生都可以辩论,老师不得骂学生。这是公元1175年,比我原来看到的波兰的学术讨论早三百年。所以,我很高兴。
国外的学术中心,哪个中心这一条执行得好,这个中心的学术成果就多。我总宣传这一条,提错误意见的人,对最后得到的正确结论也是有贡献的,人的思维是集体的。
1984年1月《自然辩证法通讯》朱长超的文章和1987年12月《哲学研究》皮亚杰发生认识论的讨论,都提到意识由感性到理性,由集体意识到个体意识的转化。人类早期,个体意识几乎是没有的,都是集体的。蜜蜂几乎都是集体意识,没有个体。越是古老的意识,个体的水平就越低。朱长超不知是否受到皮亚杰的影响,皮的心理学不大讲社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