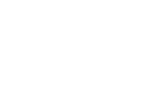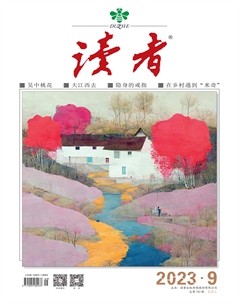衣衣不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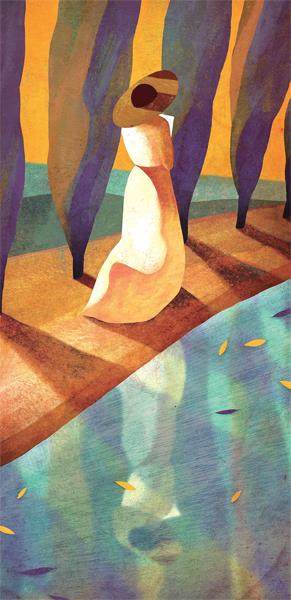
有人用日记来记录个人历史,也有人用照片记录,而我用衣服。如果人生如戏的话,我最感兴趣的既不是情节,也不是人物,而是服装、道具和灯光舞台。
看张爱玲的《对照记》,不知怎的,只觉得一个女人的一生好像最后只留下有关几件衣服的回忆。当然不只是衣服,还有那件衣服里的自己,以及自己的身体。像余光中的诗里说的,“拥抱你的,是大衣”。
我很怀念古代(所谓“古”,是指九十年前),那时候据说有一种小偷,专偷衣服。他们有一种特技,就是用长竹竿绑个钩子,从别人家的窗子伸进去钩衣服。
“他们偷衣服能干吗呢?”新新人类一定大惑不解。
啊,新新人类哪里会懂,衣服,甚至旧衣服,在那个时代都算一笔资产,值得偷,有资格进当铺,还可以当遗产分赠。
早年,在我屏东的老家,常有少数民族站在矮墙外,用腔调奇特的普通话叫道:“太太,有没有旧衣服,我拿小米跟你换啦!”
弟弟妹妹的衣服后来就都去了三地门。那个时代的衣服像日本天皇,万世一系,代代相传,其间当然可能从大衣变短袄,但常伴左右,永不灭绝——我这样说,你大概就会明白我跟衣服之间的感情了。
三十年前的一个夏天,我到台南参加一个写作营,和孙康宜住在同一间寝室(她那时还是文艺少女,在东海大学读书,现在都已是耶鲁大学的东亚系主任了)。我当时已怀胎三月,人萎萎蔫蔫的,她当然看出来了。不久以后,知道的人就更多了。于是,周围一时布满关爱的眼神。“下了课你到我家来,我有东西给你。”说这话的是谭天钧大夫,她是当时旅美华人中有名的医生,专攻小儿癌症,但那段时间她因陪夫婿而回台湾小住。
我不知道这个名满天下的女医师有什么东西要给我,我们两个人所学的东西相差太远。

登录后获取阅读权限
去登录
本文刊登于《读者》2023年9期
龙源期刊网正版版权
更多文章来自

订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