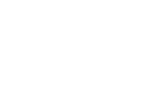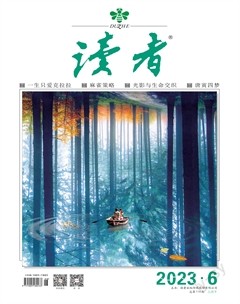1
找我倾诉的孩子,大多怀着深沉的心事和伤痛,有相当一部分患有焦虑症、抑郁症、厌食症、强迫症、双相情感障碍等常见的青少年心理疾病。孩子们很不容易,一方面受到疫情的影响,另一方面被“学历至上”的价值观所捆绑。出乎很多人意料的是,一些患有焦虑症、抑郁症的孩子,不是我们想象中成绩不好的孩子,反而是名牌学校的优等生。
我遇到的比较典型的案例是一个深圳女孩。2022年高考的前3天,她突然加我的微信,想和我聊一聊她十几年的学习经历。女孩说,她一直生活在极端的环境中。从一年级开始,父母就告诉她不能浪费任何时间,除了春节和老师批改卷子的那几天可以休息,其余的每一天,甚至每一个小时,都排满了学习任务。女孩从小就被灌输了一个理念:必须争第一。每次考试结束,如果落后了,爸爸妈妈会拉着她一起分析,制订下一个阶段每门学科的学习计划,以追求真正意义上的完美。
一个普遍的问题是,当这些优等生进入名牌中学,处在强手如林的环境,不再能轻易取得好成绩时,很容易就把自己贬低得一无是处。很多优等生跟我做访谈,会形容自己是“白痴”“笨蛋”。他们的成绩已经排在同龄人的前列了,但他们仍不满意。他们的身体会出现失眠、焦虑、无法集中注意力等症状。这时候,如果父母再不理解,依然给他们施加压力,孩子就很容易崩溃。
比如,刚才提到的那个女孩,上到初中,就出现了病理性的强迫症。考试时,她会反复检查试卷上的信息有没有写对。后来,她进入高中理科重点班,每天只睡4个多小时,凌晨4点就起床看书。
我发现陷入这种状况的孩子,有一个普遍的共性,他们的父母大多是“70后”“80后”中的“考一代”,曾经通过读书改变阶层。他们会形成一种教育理念,把孩子的价值和成绩完全画上等号,并不断地告诉孩子,读书就是为了将来去好学校,找到好工作,挣更多的钱,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这样一来,孩子就被套在“好成绩=好孩子=好未来”的公式里。同时,这些家长通常不允许自己的孩子失败,作为衡量标准的考试就显得非常重要。面对每一次考试,孩子经常感到胆战心惊,一旦出现发挥失常的情况,就会自我怀疑和自我否定。
当上面提到的那个女孩意识到这一点之后,她说自己进入大学,要想办法自救,把自己的强迫症治好。我听了非常痛心,一个孩子长到18岁,却带着一身伤痛。即便她最后考进了理想的大学,我也不觉得那是教育的成功。
这一年的采访中,我的另一个发现是,孩子出现心理问题越来越低龄化。之前可能在初中出现的问题,现在小学阶段就出现了,孩子表现出抽动症或者强迫行为,比如忍不住眨眼睛、耸肩膀、扭脖子、做怪异的表情、反复整理书包、检查门有没有关好……其中有一个孩子说,每次上完课,她需要花两个小时,在脑子里把老师的语气、语调,知识点全部回想一遍,渐渐养成强迫行为。发展到后来,她上厕所洗手要花一个多小时,迈步子要思考先迈左脚还是右脚,病症已经影响到她的学习和生活。
2
穿梭于孩子和成年人之间,我越来越感觉到,家长和孩子最大的分歧,在于家长试图把孩子打造成听话、用功、考高分的“机器”,而孩子则希望自己能被当作“人”来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