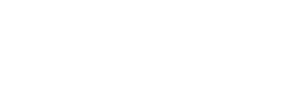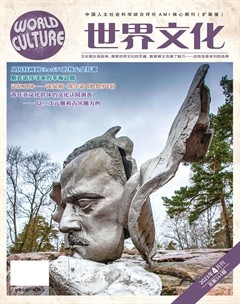女性主义与波洛克
在20世纪现代艺术发展进程中,女性主义对艺术史的介入是其中相当重要的一环。20世纪初女性主义运动波及艺术领域,1971年艺术史学家诺克林的一篇《为什么没有伟大的女艺术家?》掀起了艺术领域女性主义的探索,引发了人们对于女性艺术家的关注和思考。1999年,加拿大和英国艺术史学家格里塞尔达·波洛克(Griselda Pollock)所著《分殊正典——女性主义欲望与艺术史书写》(以下简称《分殊正典》)一书,突破了过去对女性主义研究的视角,借鉴西方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理论、后结构主义、艺术社会史、符号学等研究方法,挖掘出了一系列对女性艺术史研究更为具体而行之有效的策略,为女性主义的发展和探索开启了一条新的道路。在《分殊正典》中,波洛克着重分析了几位女性艺术家,包括卢百娜·希米德、玛丽·卡萨特等。她摒弃了“女英雄”的外衣,从客观的女性角度出发,以性别差异为切入点,阐释女性艺术家作品的隐藏含义。若想深入研究和探讨一位女性艺术家,就要结合社会语境、人生境遇和人物性格等几个方面。1980年代,弗里达·卡罗(Frida Kahlo,1907—1954)被视为女性主义艺术的代表人物,其作品不仅充满了墨西哥传统文化元素,而且显示了独特的女性色彩。
弗里达其人
1907年,弗里达出生于墨西哥,父亲是一名有着犹太血统的德国摄影师,母亲是西班牙与印第安人的后裔。弗里达有四个姐姐和一个妹妹,她與妹妹复杂的感情纠葛贯穿其一生。弗里达6岁时被诊断为小儿麻痹,导致她的右腿畸形,痛苦不堪。好在弗里达生性乐观、敢于尝试,15岁时进入墨西哥国立预科学校接受教育,梦想成为一名医生。在这里,她不仅学习知识、参加活动,还结识了墨西哥知名的壁画家迭戈·里维拉,这也成为她生命中的转折点。然而好景不长,在她18岁的一天,又经历了人生的第二个转折点——突如其来的车祸几乎让她迈入死神的禁地,但顽强的意志力助她再次重生。病床上的弗里达为了打发时间和缓解身体上的疼痛,第一次拿起了画笔,就这样开启了她的绘画之路。出院后的弗里达一边与后遗症带来的苦痛做斗争,一边用绘画表达自我。当她再次遇到迭戈后生活也随之改变——迭戈、政治和绘画成了她生活的全部。1929年,弗里达和迭戈结为夫妇,与迭戈在一起的日子是弗里达最为自由多彩的时光,他们志同道合,热爱墨西哥及其传统文化,共同支持共产主义事业, 关心现实问题和底层人民的利益。甜蜜的爱情为她的生活带来了新的生气,也为她的绘画风格带了新的灵感。
当然,婚姻生活中也伴随着很多苦痛与忧伤。一方面,车祸后遗症导致她两次流产,成为母亲的梦想破灭给弗里达带来了沉重打击,使她经受了常人难以承受的痛苦。另一方面,可能是太过自由,或是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苦难,弗里达和迭戈在婚姻中都承受了对方的背叛与伤害,导致两人于 1939年不欢而散。在分离的日子里,双方再次感受到对方的重要性并于次年复婚,直到弗里达去世,他们一直生活在一起。与迭戈复婚后,弗里达完全回归了自我的生活,她回到了小时候的家,与迭戈一起装饰出了一个颇具艺术气息的理想家园。而绘画和政治事业一直伴随着弗里达,直到最后几年她再次被病痛缠身。在1954年参加完一场游行活动后,弗里达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弗里达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弗里达的父亲、姐妹和迭戈都对她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绘画、情爱、政治和墨西哥在弗里达的人生信仰中占据着重要位置,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痛苦伴随了她一生……所有这一切构成了弗里达戏剧性的人生和独特的绘画风格。
波洛克的女性主义与弗里达的绘画
波洛克最独特的贡献在于她在重新定义正典的探索中为女性艺术家寻求应有的话语权。基于两性的差异,艺术史建立起了以“白种人的男性优先权”为前提的正典化标准。而波洛克的研究并非简单地构建一位“女英雄”作正典中的代表,她指出:“女性主义对父权艺术史的挑战固然是一种正当抵抗,然而一旦女性主义夺权,我们是否要按照父权生成的逻辑如法炮制一部‘女英雄’担当主角的艺术史呢?如果是这样,那么女性主义最终实现的目标与父权制艺术史从根本上并无二致。”所以她在《分殊正典》中首先用“逆向阅读”的方式,以女性视角去分析凡·高和劳特累克的作品,从家庭背景、精神层面等分析了他们对女性人物刻画中的内在精神特质。
而对于弗里达来说,其身体上的苦痛以及亲情、爱情、政治信仰、爱国情怀等共同组成了她的生活,注定其绘画内容集中在自我关注、亲朋好友、政治题材和民族文化等主题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