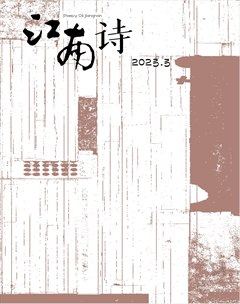怎样使诗歌写作更接近肉身和灵魂——我说的是同时接近,这是我一直思考的问题。离肉身远,写作无有趣味,缺少生气;离灵魂远,则文本不够高级,缺少意义。所以,我所着迷的理想状态,应该是理性与感性的纠缠一体,是思想与无意识的互相进入,是它们不分彼此的如胶似漆。
这样说有言不及义之感,并非要占据什么观念的高地,也不纯然是一种逻辑和理论的设计,而是写作中的真实感受。多年从事研究与批评工作的职业病,曾使我过于迷恋文本中的观念载量,但后来发现,往往是因为过于清晰和自觉的观念诉求,而使写作变得呆板,甚至产生了意义的自我抑制与自我抵消;而偶然可以放松和“不追求意义”的时候,反而会有一点不期而遇的神来之笔,让句子有点意思。
显然,意义的减载和意趣的增加,两者之间的某种辩证关系,可能构成了某种写作的奥秘。这是感性与无意识被解放之后的意外之喜。我用了很多年才意识到这一点,但还只是意识到而已,还没有很好地实现解放,而只是偶尔会有一点点临界的体会。
这构成了当代诗歌,或者诗歌的当代性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同时强调“有意义”和“有意思”——甚至后者的权重要超过前者。“有意思”是趣味性的东西,纯然诉诸于直觉印象、错觉反应、难以解说的无意识经验与活动,它是意趣的难以言传,与灵犀的不可言喻,它有时可能并没有清晰的概念性“意义”,但却令人忍俊不禁,叫人怦然心动,让人感到萦绕于心,挥斥难去。
其实,唐宋诗歌中已经大量写到无意识的东西,或者具有无意识支持的日常经验。“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陆游的《游山西村》中明显具有这样的意味。孟浩然的《宿建德江》中“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亦庶几近之。刘长卿《寻南溪常山道人隐居》诗:“溪花与禅意,相对亦忘言。”大约也有这样的意思。“禅意”与“言说”之间有一个近似与德里达所说的“延异”,言近意远,言不及义,“说时迟,那时快”之类,均是说“言与意”之间的不同步或不匹配。王维的“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甚至连主体也是悬置的,这人语只是声音,而并无意义。
但这些或许有强加于人的意思,用无意识来解释,不一定周全,很多东西有我们现代的投射与理解。至宋代,诗歌偏离了唐人的情志,渐渐注重说理,未免枯燥。不过宋人亦有自己的解决方案,就是在“理”字上再加一个“趣”字,有了“理趣”,事情就好得多。用宋人包恢的说法,“穷智极力之所不能到者,犹造化自然之声也”,这种境界谓之“状理则理趣浑然”(《答曾子华论诗》)。这样说还是有含糊其辞之嫌,给一个现代的解释,其实就是将枯燥的议理与无意识的经验加以结合,便会有令人豁然开朗之境。这方面,苏东坡做得最好,他总能够将说理化于无形,将摸不清楚的道理化为“直觉之物”。“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