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自己的写作,从严格意义上,或者说,从进入公众领域的层面,大约开始于在《书城杂志》连载的“过去时代的诗与人”系列,后来它们结集成《既见君子》那本小书。当然,在那之前也一直在写,写诗,写书评,写时评和影评专栏,写论文,但都散乱,那种散乱的写作大多是一种消耗,是学徒期的左冲右撞,不能构成和自我生命的互补。《既见君子》对我自己而言是一个新的开端,想想动笔的时候,尚且还是二○○八年初,一晃十五年过去了。回想起来,这本小书是在一种非常寂寞也非常混乱的心境中开始的,而每写完一篇,都会增加一分安宁。我一直很怀念那样的状态。
《既见君子》中那篇同名文章就是在写《诗经》,我挑出《诗经》中提到“既见君子”这句话的一些篇章,用一些我觉得尚有意思的体会,把它们串联在一起。如果说《既见君子》的写法还是偏重比兴,天上地下,东一句西一句,是某种意义上的性情文章,那么等到后来二○一六年春天,《文汇报》笔会副刊的周毅约我开一个有关《诗经》解读的专栏时,我的想法也开始发生了变化。这次我希望可以用赋的方式,老老实实地一首首把《诗经》中我喜欢的诗篇讲清楚,且讲出前人所未讲之处,不光是疏通文句,更要贯通诗意,讲明这些诗何以成为诗,并从中体味诗。所以我要做的就不是写我自己,而是写这些诗;也不是求一个正解,而是求得某种属于诗的统一,是文字、句法、音韵、气息、意思、感情等多方面的统一。我觉得最好的诗未必能解释,但都是可描述的,只要我们信任那些诗人,信任他们写下的每一个字词,每一处沉默,信任它们一同所构成的那个完美坚实的存在,而诗不单是想象和哲思,诗也在这些踏实细密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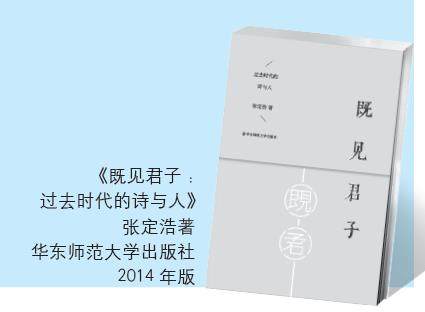
写《诗经》文章的时候,紧挨书桌的床头摊了十几本注疏集释,电脑上又同时打开着一堆电子版的相关文献,也在知网上看一些新的文章,关于某个字、某个句子,关于某个器物,每一句都是各家说法都看一遍,比较,参详,但并不是要做裁判员和调解员,而是看完之后再自己慢慢想,想着想着就会有一点新东西出来,仿佛离那个写诗的人又近了一些。这个过程就是把自己放弃的过程,因为自己的一点点诗意是不重要的。知道自己是不重要的,随后才有切实的工夫,去吸收、感受、思索和书写。朱东润《诗心论发凡》:“治诗三百五篇之学者,则必博搜冥考,追求百家之遗说,折衷于事理之当然,而后能惬心贵当,怡然理顺,不得以一先生之说自囿也。”
这样的写作,断断续续进行了两三年,其实也不过就写了六篇。后来周毅忽然去世了,没有了她那样永远怀揣“肯定的火焰”的督促者,我也就懈怠下来。加上又有其他写作任务缠身,有关《诗经》的写作热情就消退成我笔记本电脑中一个长久不再更新的文件夹。
直到二○二二年。对每个中国人来讲,这一年都是一个难忘的年份。而对我来讲,这一年的难忘收获是终于重新拾起搁置许久的《诗经》解读,并再次在我喜爱的《书城杂志》上连载。“风雨如晦,鸡鸣不已”,鸡鸣并不是为了对抗什么,而只是对于如晦风雨的漠视。
二
诗似乎是不可谈论的,但至少每一首好诗都经得起反复地读。我们今天的很多人,尤其是在离开学校之后,有时候会疑惑为什么还要读《诗经》,其价值何在?对我而言,单纯的审美或陶冶性灵之类的理由,是远远不够的,也没有力量,因为任何愿望,一旦仅仅出于某种理由,它就一定可以因为另外更重大的理由被抛弃。而一个人最终不可抛弃也无法抛弃的,是他还没有获得之物,也就是他所欠缺之物。某种程度上,诗对我而言就是这样一种尚未获得、始终在前方的存在。我总是带着问题和欠缺感,去读那些过去的诗。而那些过去的诗也得以在这样的阅读中转化成即将到来的诗。从而,让自己的写作本身,成为一种更为积极的阅读,成为一种对于“为什么要读诗”的回答。
唯有如此,阅读《诗经》才不至于沦为一种玩弄风雅之事,不至于成为一种逃遁,抑或一种现代生活的对立面。
倘若单纯从鉴赏审美的角度去看《诗经》中的一首首诗,就好像在博物馆里看一幅幅画,其中的典故风物人情,以及用笔着色的曲折有度,都可以作很多社会学和文化史乃至艺术史上的解释,这些本身都是知识,也很好,但最后,和我们自己没有关系。我理解的《诗经》,恰恰不是知识,不是能够用搜索引擎搜索到的答案。若是谈到古典修养,在我看来,能够背多少古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最后究竟是被什么东西打动的。
威廉·布莱克有一首写弥尔顿的诗,里面有几句是这样的:“但是弥尔顿钻进了我的脚;我看见……/但我不知道他是弥尔顿,因为人不能知道/穿过他身体的是什么,直到空间和时间/揭示出永恒的秘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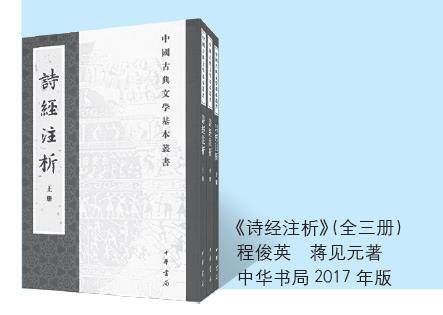
一個人被什么东西打动、穿过,其实自己最初是不知道的。而类似诗歌鉴赏辞典之类的存在,抑或某些诗歌赏析文章,是预设自己从一开始就什么都知道了,这种预设在我看来稍微有点问题。那些能够被感受但不能自知的东西,都和自己的生活有关;那些自以为知道的,其实只是和自己无关的知识。而把那些穿过自己身体的东西,重新在回忆中审视,并且慢慢地尝试去理解它,这就是《诗经·大雅》里反复讲到的“缉熙”,所谓“日就月将,学有缉熙于光明”,所谓“缉熙敬止”,这些天地自然的光,如何一点点成就到人的身上,并让一个人成为值得敬重的人,在我看来,这个过程才是诗。而这种穿过身体之物,在不同年龄段是不一样的。比如二三十岁的时候,或许是“既见君子,云胡不喜”,到了四五十岁,也许就换作“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