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越长越大,童书也越积越多,次子小学一毕业就处理掉了一大批。不过,总有那么一些舍不得的,也总觉得应该留下点什么,于是试着写下这篇札记。边读边写,仿佛又回到了亲子共读的金色长河,亦仿佛重温了一遍童年。
鼠目有情,鼠眼有光
贼眉鼠眼,鼠目寸光,硕鼠硕鼠,无食我黍,老鼠过街……人类社会里鼠类的形象实在有些不上台面。然而小孩眼里万物有光,人类鼠类,皆我族类。周氏兄弟成年后均念念不忘儿时看过的“老鼠娶亲”的年画,鲁迅回忆说“那时的想看‘老鼠成亲’的仪式,却极其神往”(《狗·猫·鼠》),还养过一只能为他舔食墨汁的小隐鼠。
《鼹鼠的故事》是捷克艺术家兹德内克·米勒(Zdeněk Miler)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在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创作的系列动画片及绘本,由波希米亚走向世界,早已是儿童故事的经典。土里来土里去的鼹鼠到了米勒笔下纤尘不染,大眼睛温和灵动。《鼹鼠帮兔子找妈妈》里,与妈妈走散的小兔子痛哭失声,哭醒了在地下睡得正香的鼹鼠。刚会说话的长子读到这页便拿起书来,让我抱着那书,说,兔子要妈妈啊,你抱抱它吧。《鼹鼠与老鹰》里鼹鼠自洪水中救出老鹰宝宝,一手把它养大,母性十足。《鼹鼠与电视》讲了个电视“中毒”的故事。小动物们有了电视就像得了宝贝,鼹鼠看累了回去睡觉了,大耳鼠、兔子和刺猬它们则看得夜以继日、雨雪无阻,直看到藤蔓缠身、动弹不得。后来鼹鼠锯开藤蔓解救了它们,还推来一车哑铃让大家锻炼身体。《鼹鼠当医生》里大耳鼠病了,鼹鼠从欧洲跑到非洲,又跑到大洋洲、北极洲和北美洲,满世界给大耳鼠找药。一路上鼹鼠曾经掉到狮子头上,也曾被鲨鱼吞进肚里,还见识过会吃虫的猪笼草、闻一下就让人失去知觉的毒花……世上无奇不有,鼹鼠有惊无险。最后鼹鼠还是回到了故乡,在老橡树下采到了药。《鼹鼠的故事》温情脉脉、从容舒缓,也流露出了波希米亚人乐天知命、与世无争的天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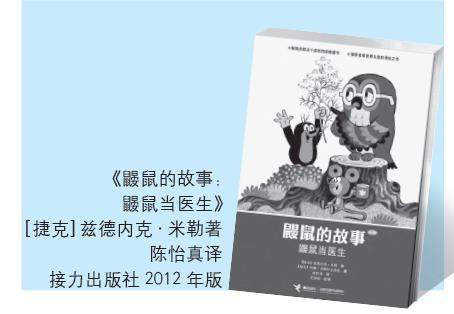
卡夫卡发表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小说《地洞》的主人公就是个鼠类(大约是只鼹鼠,卡夫卡在致友人信中提到过自己像只打地洞的鼹鼠),首鼠两端,孤立绝望,患得患失,惶惶不可终日。半个世纪后,赫拉巴尔写了一本《过于喧嚣的孤独》,书里的老鼠成了精般参与到废纸打包工汉嘉的生活当中,见证了他在地狱里寻觅天堂的另类人生。《鼹鼠的故事》中,创作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鼹鼠在城市》《鼹鼠的梦》仿佛与这些文字一脉相承,阴翳多阳光少,更像是给大人看的。《鼹鼠在城市》里森林被砍伐光了,鼹鼠与伙伴们不得不体验了一把钢筋水泥的城市生活,到最后还是义无反顾离开城市,奔向远方。《鼹鼠的梦》讲述一个大人梦见没电没水没汽油了,天寒地冻,鼹鼠帮他生火取暖,春天到了,他与动物们过着原始的生活……醒来发觉是个梦,长出一口气。等他来到加油站却发现真的没油了,而梦里的锤子亦出现在现实中,令他混乱且沮丧。生活中的荒诞与丧失多了,童书亦不免染上灰色。《鼹鼠的梦》只有动画没有绘本,或许也是由于太过灰暗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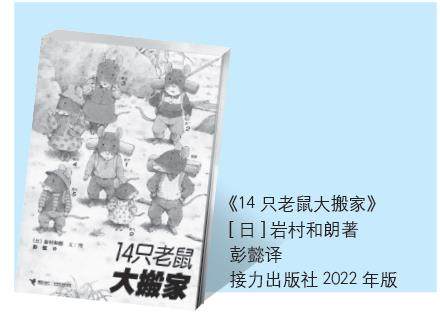
波希米亞鼹鼠横空出世,无亲无故,无牵无挂,岩村和朗笔下的“14只老鼠”系列绘本则讲述了一个老鼠大家庭的故事,里面有爷爷奶奶爸爸妈妈,还有六个男孩四个女孩。岩村三十六岁离开东京迁到枥木县益子町,隐居杂木林中,亦耕亦读亦画,也给了他的孩子们一个野生的童年。“14只老鼠”系列绘本从一九八三年画到二○○七年,皆创作于大自然中,细腻不留白,本本精彩。《14只老鼠大搬家》《14只老鼠的晚餐》……都是左右合起来成一大页,严丝合缝,构图精妙,每大页下面又都有一行字,问那个睡懒觉的是谁,那个戴着漂亮帽子的是谁,那个差点儿坐了个屁墩儿的是谁……两三岁的小孩很快就能找到答案,开心得手舞足蹈。“古里与古拉”系列绘本亦以老鼠为主人公,作者中川李枝子接受采访时说:“想做一个让孩子们吃惊的大蛋糕,就得用一个大鸡蛋……为了显得鸡蛋大,古里与古拉就设定成了小小的‘野老鼠’。”(《吓人的大蛋糕》,《朝日新闻》2021年5月4日)这对双胞胎野老鼠深得幼儿喜爱,开了“古里与古拉”系列的先河。
鼠目有情,鼠眼有光。
成长,历险
人的成长或许是个漫长的过程,或许缘于一个事件,或许就是一瞬间,刻骨铭心,成长小说亦自成一类。张爱玲在一九六三年六月二十三日致友人信中谈及将自己的英文小说《易经》改译成中文,说《易经》“并不比他们的那些幼年心理小说更‘长气’,变成中文却从心底里代读者感到厌倦”(《纸短情长:张爱玲往来书信集1》)。“他们的”可用“英语世界的”或“西洋的”来置换,私信里张爱玲一向将他们与我们分得清清楚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