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六年,著名作家郁达夫出任福建省参议兼公报室主任,初履斯地,应该颇为愉快,因为他很快在创办不久的《逸经》半月刊(1936年3月创刊)第九期发表了《饮食男女在福州》一文,并成为饮食文学文化史上的经典篇章。文章一开篇就说:“福州的食品,向来就很为外省人所赏识,前十余年在北平,说起私家的厨子,我们总同声一致地赞成刘崧生先生和林宗孟先生家里的蔬菜的可口。当时宣武门外的忠信堂正在流行,而这忠信堂的主人,就系旧日刘家的厨子,曾经做过清室的御厨房的。上海的小有天以及现在早已歇业了的消闲别墅,在粤菜还没有征服上海之先,也曾盛行过一时。”这一段话,也可以作为展开闽菜出闽入京叙述的楔子。
一
李一氓先生说:“限于交通条件、人民生活水平和职业厨师的缺乏,跨省建立饮食行业是很不容易的。解放以前大概只有北京、上海、南京、香港有跨地区经营的现象。”(《饮食业的跨地区经营和川菜业在北京的发展》,载《存在集续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晚清民初,饮食跨省传播出现了两个条件最好的地方,一是北京,二是上海。北京是政治中心,各省人等云集;上海是商业中心,更是五方杂凑,各系菜馆,自然应运而生。根据掌故名家金受申先生的说法,北京闽菜馆乃至其他南方菜馆,是清末民初才开设,而起初似乎并不待见:“各南菜馆,从清末民初,才渐渐开设……‘福建馆’,纯粹的很少,能做福建菜的几乎没有,即如羊肚菌、烧四宝,又岂仅福建馆所独有的呢!”(《老北京的生活》,北京出版社1989年)
其实未必尽然。据刊于嘉庆二十二年(1817)的得硕亭《草珠一串》(又名《京都竹枝词》),其“商贾门”有曰:“苏松小馆亦堪夸,南式馄饨香片茶。可笑当炉皆少妇,馆名何事叫妈妈(宣武门外有妈妈馆)。”“饮食门”有曰:“华筵南菜盛当时,水爆清真作法奇。食物不时非古道,而今古道怎相宜。”更早的创作于乾隆六十年(1795)的杨米人的《都门竹枝词》,也有一首提到苏式馆子:“羊角新葱拌蜇皮,生开变蛋有松枝。锦华苏式新开馆,野味输他铁雀儿。”(路工编选《清代北京竹枝词》,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均足以说明清中期南味已流行京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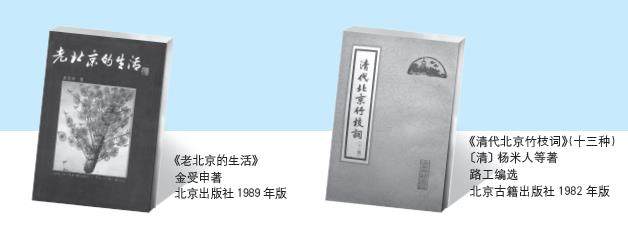
据杨度在北京《晨报》的专栏文章《都门饮食琐记》,闽菜入京,始于小有天,然后“引燃”了醒春居以及后来更有名也更大型的忠信堂等,闽菜馆由此进入京华盛世,并为郁达夫等所乐道;历史的经验也表明,一个菜系的发展,往往有赖于某些关键人物及个别顶级菜馆的引领,比如谭延闿谭府菜之于湘菜,谭家菜、太史菜之于粤菜,黄敬临姑姑筵之于川菜,等等。闽菜在北京的发展,郑大水及其忠信堂的引领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福建菜馆最初在京中开设者为劝业场楼上之小有天,菜以“炒响螺”“五柳鱼”“红糟鸡”“红糟笋”“汤四宝”“炸瓜枣”“葛粉包”“千层糕”著名,兼售肉松,亦著名。当时生意极佳,遂有大规模之闽菜馆名醒春居,在大李纱帽胡同开张,肴馔极可口,而以“神仙鸡”“生蒸鸡”“纸包笋”“五柳鱼”“锅烧鸭”最为著名。资本雄厚,生涯极好。嗣因营业发达,又在东单二条开一分号,不久因内部关系营业不振,小李纱帽胡同之醒春居先歇业,东单二条继之闭歇。劝业场被火,新世界成立,小有天即迁入。东安市场当时亦有小闽菜馆名沁芳楼,不甚佳。(《都门饮食琐记》之八,《晨报》1926年12月6日第6版)
(按,北京劝业场1905年因清政府建立商部而建设,其被火在1908年,那小有天至迟在1908年前即开设了。)
过了两天,杨度继续撰文鼓吹闽菜:
忠信堂开张后,始又有大闽菜馆,主之者郑大水,为闽厨之最。以整闽席著名,外会及宴客者,日常数十桌,又夺东兴楼之席,用伙计至百数十名。著名菜有“鸭羹粥”“炒战血”“红糟鸭”“炉炒鱼”“清蒸鲳鱼”等为最。年来生涯稍不如前,已在天津分一分店,颇发达。春记饭庄在米市胡同,亦以闽菜名。继因营业佳,迁至南新华街,以局面大,渐不支,已闭歇久矣。香厂曾有一三山馆,纯系闽菜,有“鸡塔”及点心数种,为不普通之闽菜,嗣因偷电被罚倒闭,现迁六部口游园开一南轩,仍为闽菜。东四七条亦有小有天。(《都门饮食琐记》之九,《晨报》1926年12月8日第6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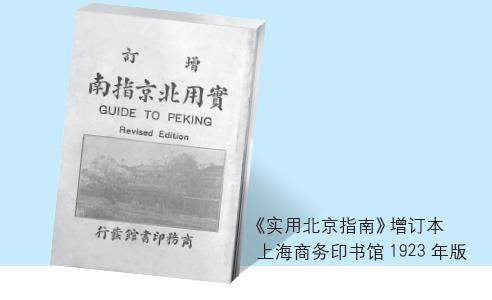
至于京华闽菜之美,则孙福熙主编《北新》文章之述:“清华园厨房特做的高丽馒头,闽菜馆忠信堂太和春等的葛粉包,尤其是在六部口小有天吃的千层油糕,都是引人超脱这娑婆世界而入甜美的乐园的……牡蛎在法国是名产,只是加柠檬汁生吃的,不必论,吃其余贝类也不及中国,闽菜中的红糟香螺何等的用功夫,使他如此的香美。”(春苔《味儿—烹饪研究引》,《北新》1927年第20期)
诸家之中,忠信堂应该开设较晚,因为在中华图书馆编辑部一九一八年版的《北京指南》尚未见忠信堂的身影,倒是另列出一家京华春,见其第五卷“食宿游览乙(十一)”:“闽菜馆:小有天,劝业场;京华春,煤市街。”稍后的《北京便览》仍无忠信堂,倒增加了中有天,不知何故。“中有天(闽菜),虎坊桥;京华春(福建),煤市街。”(姚祝萱编辑《北京便览》,文明书局1922年)再稍后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实用北京指南》仍没有忠信堂,倒增列了一家涌泉居:“小有天,香厂游艺园;京华春,福建河南,小椿树胡同;涌泉居,闽菜,东四北大街。”(《实用北京指南》增订本,第八編“食宿游览·饭馆”,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年)直到一九二八年第一九五七期《北洋画报》李三爷的文章《西长安街之闽菜馆》出来,我们才在大众媒体上再见到忠信堂的身影:
西长安街自去岁以来,饭馆酒楼,如雨过芽见,怒放不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