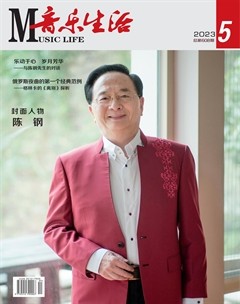“气”这个名词或概念初听起来,是让人甚觉缥缈无踪的。的确,在通常情况下对于人的视觉感官而言,它就是飘忽不定、无形无状的一个代名词,但中国人却很神奇地将其纳入到自己的艺术审美语境当中,从某种至高无上的视点[1],赋予了“气”以某种绝妙的艺术美感的价值定位。从艺术哲学角度来说,“气”与“道”一样,也是中国人在传统的艺术审美领域所积极关注和認知的、超越于西方“美”范畴的一个重点审美论域,著名美学家叶朗先生对此已有过明确的学理话语界定[2],这也是笔者对于“气”审美范畴进行重点思考并要积极描述它何以在音乐艺术中显现等问题的一个立论基础。
一、“气”的表象对于音乐人意味着什么
总体来说,在音乐人的主体性中,有着人类极其敏感的内心和极强的艺术审美感悟力的特点。音乐人在自身专业的修治之外,应该是最易虚静、平心地感受大自然中“气”的流通与交融情状的群体了。在自然界中,应该说“风儿”是“气”之表象的最为普遍和常见的样子,风儿吹过的一切事物,都会在其气息的疾徐流变中相应地显示出飘零、摇曳之姿。“气”的各种奇妙运势变换的种种情形,会通过如此这般的、凭借他者自然回应的方式而同频传达给外界,内心细腻、善于观察的人们,便以此可知其内在的力道和现实的存在性状。
由此,在中国古典审美叙事的经典情境中(如俞伯牙在其师连成先生的智勇运筹下,独自凌风观海以思求琴道升华之方),或在一些世界音乐论域里的音乐文艺片或记录影像里(如记述东南亚特性乐器演奏技艺修为路途上某种主体的领悟与突破),都常常会表述某个有着绝好艺术悟性的、视音乐艺术如同生命般的习乐者或爱乐者的相关轶事题材,也即他们是如何在细致入微、沉浸式地观察了“风吹万物”之变幻莫测的行迹之后,忽然就以质的飞跃状态,提升了自我的音乐诠释能力、艺术修养和审美情趣。
在音乐研究的领域中,作为“气”的典型的具体表象,又常常会出现在中国历史上世代传承下来的优秀音乐典籍的传统审美命题中。这些传统审美命题,虽然存在于不同时代、不同方家之言辩中,但彼此之间有内在的学理继承性与思维连续性,充分显示出了自古到今的华夏民族在对“气”范畴的审美理解、审美看待、审美态度与审美表达上的旨趣类归感。其中知名度较高的相关审美命题有:老子提出的“气”概念[3]、中国古典美学中(如《淮南子》、王充等人)的“元气论”[4]、《管子》中有关“气”的论证[5]、特别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气”范畴及其审美命题[6]的相关的较为系统的表述文字(如阮籍、嵇康、杨泉等人的审美观念)[7],等等。
可以说,无论是自然界中“气”现象之存在表象,还是音乐界中学理式讨论下的“气”审美范畴的具体规定之表象,其实都并不存在横亘于音乐专业内外的认知违和感,因为从中国传统审美思维的精髓性而言,在主体间性中普适化的 “天人合一”的思维前提下,自然外界所属层面的表象和人所构成的社会层面及专业分工下的具体表象之间,都是由同一个根本性的目的所统摄着的,亦都是在不同地、在分有着这种根本性目的而已。因此,众表象在相互之间的关系并不矛盾对立,它们都属于“气”之审美范畴,是一体众象的一种体现。
二、作为音乐人该如何理解“气”的本质
对于音乐论域中的创作、表演及欣赏等行为主体,在接受“气”审美范畴并形成本质理解的这一问题上,笔者认为,应从三方面来提升相关认识。
首先,应继续遵循中国古人业已建立好的传统审美思维意识来延续自我认知。在上述的那些艺术典籍当中,先贤们已经对“气”审美范畴做出了深入了研究与学理规约,这是后世学人思维意识中的宝贵精神财富与精良治学经验;同时,他们给与了这一范畴极高的哲思地位,“气”是与“道”审美范畴相互密切联系着的、系列而出的同级别的审美范畴,也就是说,在西方世界两千年以来持续把“美”作为审美终极目的的时候,中国人的超越性已然将审美的眼光投放到与“道”并行的“气”范畴之中了,因此,“气”范畴同样是超越于西方“美”范畴的审美思维意识,它的存在价值本质上也反映着“道”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