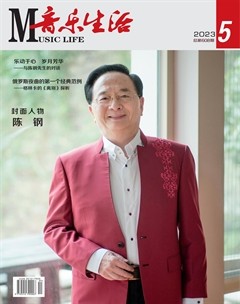在中国文艺蓬勃发展的今天,苏州评弹作为曲艺界的一朵奇葩,面临着文化快速消费时代的新形势,挑战与机遇并存。传统曲艺的传承同样需要有新鲜血液的注入,而承载体最强大的则是广大的学生群体。在我国各大高校几乎都开设了声乐表演或声乐演唱的专业课程,以及与之相对应的声乐作品赏析等选修课程的今天,笔者认为,开展民族传统曲艺艺术在声乐课程中的学习,是非常有必要的。传统曲艺的表演形式,能兼容声乐演唱技巧,拓宽声乐教学思路,使教学内容的质量得到提高,从而吸引学生的兴趣学习,造就音乐人才的全面性。因此,构建和谐并行、创新发展的文化生态与教育事业的优化路径,就是传统曲艺与声乐教学的融合发展。
一、历史与当下:苏州评弹的古今概况
无论哪种文化,都形成于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中,人们根据不同的自然条件与物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组织结构,因而创造出了各具特色的文化,其体现的精神、表现的特点和发展的态势各不相同[1]。清中叶以来,评弹文化逐渐“盛于江南”,这些江南市镇既是商业和手工业的商品集散地,也是评弹艺人演出的“书码头”。[2]地处苏东南地区的苏州,独特的地理条件使其农产品丰富,历史上就有“鱼米之乡”的美誉。苏州是吴文化和江南文化传播的中心地带,曾有“才子佳人出江南”之誉。苏州在清代的“康乾盛世”中,进一步发展了经济文化。“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人文积淀,才有了“昆曲”“评弹”等艺术珍品的孕育。苏州评弹凭借“小桥流水人家”“文人墨客吟诗作赋”这一苏州特有的人文空间,逐渐加深了苏州评弹的影响力。苏州评弹是由评话和弹词组合而成,用苏州地域方言演绎,是浓缩了苏州地方文化的精华,也是当代吴文化的一种呈现。评弹分布的地方主要在江南一带,也是因为其语言的行通范围所致:“过远之处听不懂苏白,去亦徒然”。[3]
苏州评弹最早发源于明朝,后来流传于清代。清代早、中期,政府政权稳定,经济繁荣,社会大众在精神文化层面的需求逐渐丰富起来,为了满足社会不同层次人群的需求,苏州评弹既贴合大众,又具有文艺气息的说唱艺术被更多的人所接受,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市井居民,都对评弹这种表演形式乐此不疲。于是,从清乾隆到嘉庆、道光年间,苏州评弹迎来了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有群众基础的评弹,这时候发展的余地就更大了。这一时期,“陈”“俞”“茂”“陆”四大流派的声名鹊起。“陈”是陈遇乾,“毛”是指毛营佩,“俞”是指俞秀山,“陆”是指陆瑞庭,被大家称作评弹“四大名家”。四人的表演方式各成一派,各成体系,深刻影响了评弹事业在后世的发展。苏州评弹继续发展到清咸丰、清同治年间,此时评弹艺人把主要精力放在了说唱内容上,并在原有内容的基础上进行了增补,由以往的篇幅较短,增加到了篇幅较长的评弹作品;评弹艺人在“说”的比例上更加讲究,缩减了演唱段落,“板腔体”在这个时候也更加成熟地发展起来。[4]此时评弹界除了之前的陈遇乾、俞秀山等人形成的“陈派”“俞派”,”又产生了新的风格流派,以评弹艺人马如飞所代表的“马调”独当一面。他吸收当时流行的花鼓调、东乡调、滩簧调、吟诗声调而创造质朴明快的“马腔”,是基本唱腔之一,与“俞调”齐名,“马调”的曲风较为豪放,但豪放中见功力细腻,深得人们的喜爱。[5]苏州评弹发展到清代末期,发展速度比较缓慢。而马如飞为此时的评弹发展做了许多贡献,如评弹历史上影响最大的社团组织“光裕社”在战争中被毁,许多评弹艺人推举马如飞重建光裕社。[6]直到民国时期,评弹在上海迎来了“黄金期”。彼时的上海经济文化繁荣,作为全国文化娱乐中心,曲艺界为满足大众娱乐需求,评弹艺人开设了多家书场,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评弹依靠其活跃多变的艺术风格脱颖而出。
苏州评弹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在面临新挑战的同时,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此时的演出场地——书场,已经发生了改变,经济发展影响评弹的生存空间,书场的经营维系十分艰难,苏州评弹进入了迟滞的发展时期。到20世纪六十年代中期,评弹艺术在经济稳定发展的情况下重新兴盛起来,更多的听众也带动了书场的开办。苏州评弹中有极具时代特色的曲目,如《刺绣女工心向太阳》。中国传统的文化环境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苏州评弹也遇到了和很多传统艺术一样的困境,评弹艺人头上萦绕不去的问题就是如何传承和发展。随着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推进,苏州评弹2006年被国务院授予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苏州评弹成功入选“非遗”名录是对苏州评弹较为有力的保护。
二、观念与探讨:苏州评弹融入声乐教学的可能性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苏州评弹无论从评弹的曲艺本体,还是从评弹的生存空间来看,都是以活态的形式呈现出来的。在笔者看来,通过各种形式实现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目前对传统曲艺最直观的保护方式。当然,评弹的发展与保护不可孤立来看,如果失去了保护就没有发展了,如果没有保护约束就“发展”了,那对传统艺术来说,就可能是一种摧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