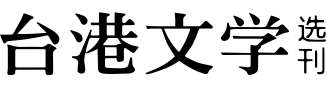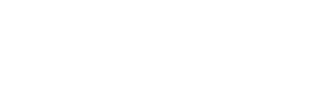1936年,林语堂在美国着手写一部有关苏东坡的传记。后来他用英文完成了《苏东坡传》,英文名字为The Gay Genius。《苏东坡传》是林语堂颇为偏爱的一部作品。传记关注现实与道德关系的重大议题,描写了传主苏东坡与时代政治风云的关系,生动地展现了苏东坡的人格风范和精神气质。此外,传记还糅合了林语堂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带有强烈的理想主义情怀,呈现了以苏东坡为精神参照的林语堂个人对于独立精神生活的热烈向往、追求和讴歌。
一、为什么要写《苏东坡传》?
为什么要写《苏东坡传》?林语堂曾说:“我写《苏东坡传》并没有什么特别理由,只是以此为乐而已。”[1]然而,从萌发写作念头到传记出版,林语堂大概用了11年。这期间,林语堂把有关苏东坡的珍本古籍以及相关参考书都带在身边,以此为学、以此为伴。他把传记的重点置于苏东坡的人格魅力上,将苏东坡丰沛的创造力、守正不阿的品格和放任不羁的性情铺展开来。在他看来,“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酿酒的实验者,是工程师,是假道学的反对派,是瑜伽术的修炼者,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饮酒成癖者,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2]然而,林语堂仍然觉得这些都是只言片语,无法勾勒出苏东坡的全貌。他认为,真正能概括苏东坡的只有这一句——“我若说一提到苏东坡,在中国总会引起人亲切敬佩的微笑”。[3]这里,林语堂试图通过苏东坡在中国社会的影响力,牵引出一个广阔的历史视野,一个意义重大的历史主题,一种向历史学习的态度。
当人们不再依据久远的史实去理解历史人物,而是从自己切身的感受去思考历史人物,那么人们与历史的对话便真正地展开了,他会在自我理解和自我意识方面取得新的突破,也会在观照历史、社会和个人的关系中获得认识历史的新高度。毫无疑问,撰写《苏东坡传》需要依靠强烈的独立精神、坚定的决心、深入持久的洞察力,这对于林语堂而言是丰富有趣且充满挑战的。林语堂不断地跟北宋时期的政治生活和苏轼的人格气质发生接触,推进了他对于历史传统、民族精神和政治德行的认识,使写作在很多方面可以做到归于其个人的道德生命,去实现一种发展着的自由精神。正因此,写作《苏东坡传》变成了推动林语堂个人主体性上升的一个过程。所以林语堂才会以调侃的语气说道:“现在我能专心致志写他这本传记,自然是一大乐事,此外还需要什么别的理由吗?”[4]
但是,要写出这种传记还是很难的。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理解苏东坡这个历史人物。林语堂直言:“元气淋漓富有生机的人总是不容易理解。像苏东坡这样的人物,是人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的。对这种人的人品个性作解释,一般而论,总是徒劳无功。”[5]苏轼是一个多才多艺的天才,他深厚广博的学养、高度的智力、诙谐风趣的语言、天真烂漫的赤子情怀,早已成为固定形象,一直决定着人们对他的理解。因此,如何突破固定模式去做传记便成为首要思考的重点。对此,林语堂不但要认真研究和处理大量的历史事实,而且还需要清空一些历史材料。这样做的目的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让写作变得简单明了。然而这又意味着什么呢?历史学家卡尔曾经非常羡慕那些从事古代史写作或中世纪史写作的人。他曾分析指出,这些历史学家之所以能耐如此之大还是源于他们对研究主题的无知。卡尔认为对“无知意识”的培养是历史学家的重要任务,这意味着历史学家可以依靠个人判断力来处理思维与历史事实之间的关系,形成一种平等的、互动的关系。这听起来似乎有些不可思议。事实上,卡尔所说的这种“无知的意识”正是一种智慧的勇气!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不沉溺于历史经验,不屈服于已有的历史成果,摆脱史实的压迫感,更多地将精力投入在好奇心上,更好地处理自己和历史的关系问题。也只有这样,史学家才能越来越接近自身的时代,越来越敢于表达个人独特的历史观念。在卡尔看来,“历史学家与历史事实之间彼此互为依存。没有事实的历史学家是无本之木,没有前途;没有历史学家的事实是死水一潭,毫无意义”。[6]他坚持认为“历史是历史学家与历史事实之间连续不断的、互为作用的过程,就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休止的对话”。[7]
第二个问题是我们如何理解林语堂对于苏东坡的偏爱之情?尤其是他对王安石的评价与中国通史所存在的矛盾之处。陈歆耕曾指出《苏东坡传》存在误征某些不实史料,在苏东坡与王安石之间褒贬失當。他认为苏洵的《辨奸论》存在真伪问题,而林语堂不厌其烦地对《辨奸论》加以征引,用以诋毁王安石的人格形象,实在是有失一位大师级作家和学者水准。[8]赖勤芳则认为,尽管《苏东坡传》是一部关于苏东坡的历史人物传记,但它的“自传”色彩极为浓厚,渗透出一种对自我人格精神的反观及合理性寻绎的特点。[9]曾有作家评价:“林语堂的《苏东坡传》是一个赤子写另外一个赤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