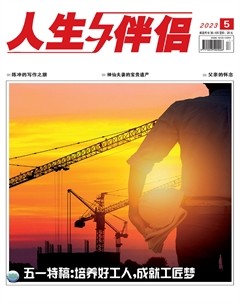2023年3月的最后一天,是陈冲主演的电影《忠犬八公》首映的日子。这个关于爱与失去、忠诚与守候的故事,从“八公”故事的真实发生地日本,经过美国版的演绎成为经典,又漂洋过海,改编成中国版。
在片中,陈冲饰演一位开便民小卖铺的重庆妇女李佳珍,平素对丈夫、大学教授陈敬修(冯小刚饰)诸多抱怨。外出考察的路上,陈敬修遇见一只中华田园犬“八筒”,心生怜悯将它偷偷带回了家。李佳珍对丈夫的抱怨和反对由此到达顶点。随着“八筒”逐渐被接纳,陈家的温馨故事也随之展开。
戏外,陈冲与冯小刚鲜少交流。冯小刚爱抽烟,一根接一根,陈冲却闻不得烟味,她故意躲得远远的,有意将这种“細碎的抱怨”放大——这是戏里李佳珍对丈夫常有的态度。而这些都不妨碍李佳珍在陈冲眼里是一个幸福的女人,在这么一个小土坡上升腾起一个便民铺,成了一个小世界的社交圈中心,往来的人间故事都在这里汇集。她被丈夫孩子爱着,日常的碎碎念也是平凡幸福的一种表现。
影片拍摄于2021年春天。这一年,对陈冲而言意义非凡。那时疫情还不见尽头,亟需一些温暖和治愈的力量。因为拍摄《忠犬八公》,她回到了父亲的故乡重庆。每日学说重庆话,让她回想起小时候爷爷与她说话的温暖片段。拍摄间隙,她还四处走访,找寻父亲昔日生活的足迹。
也在这一年,陈冲深爱的母亲因病去世,她强烈地感受了爱与失去,也重新审视生命的意义。“我现在依然在过程中,在慢慢接受母亲离开的事实。但有些东西,失去就是永远失去了。”她告诉记者。
而写作可以将记忆定格。陈冲开始系统写作,也始于2021年。2021年7月起,陈冲开始在《上海文学》发表系列散文,在这份文学月刊中,她勤力保持着每期一篇的更新频率,每篇文章洋洋洒洒都超过万字,17个月里,她累计写下20多万字。
“记忆,像早晨爱人离别后枕头上柔软的凹印,那是他在你生命里存在过的证据……我从很年轻开始被各路记者采访,不少过去的事,已经被反复叙述,变成了翻版的翻版,连我自己也很难看清它们的原貌。也许,要保持原始的记忆,唯有不去触动它。有一日,在完全没有准备的情形下,我突然回到了一片未曾被自己过多调用过的记忆,有些只是模糊的印象,也有些清晰犹如昨天,我企图把它们写下来,或许人们能看到我在枕头上留下来的那个凹印。”在开篇《一号人物》的“前记”中,陈冲写道。
活在文字里的母亲
母亲去世后,怀念母亲就成了陈冲文章中最常出现的主题。
在《我们将死于梦醒》中,她记叙了陪伴饱受癌症和阿尔兹海默症双重折磨的母亲在病房里唱歌的片段:“记忆里那些母亲摆脱了苦难的日子,屋里总是充满了阳光,窗户很大,太阳照在她的脸上,她专注的歌声充满了少女的渴望:小鸟在歌唱,野花在开放,阳光下面湖水已入梦乡,虽然春天能使忧愁的心欢畅,破碎的心灵再也见不到春光,我走山路,你走平原,我要比你先到苏格兰,但我和我爱人永不能再相见,在那最美丽的罗梦湖岸上。她走后我才知道那是一首苏格兰民谣叫《罗梦湖》。”
在陈冲的回忆里,母亲一生最快乐的时光之一,是在抗战期间张治中将军创办的、位于重庆山洞镇的教会学校圣光中学度过的。在整理母亲的遗物时,陈冲看到一个四方的曲奇饼干盒,里面保存了一些光盘、照片、贺年卡和信件,光盘都是历年来圣光校友会的相片,信件也都是圣光同学写给她的。圣光中学到底有什么样的魔力,让母亲过去这么多年依然念念不忘,同窗的友谊持续了半个多世纪?
陈冲翻遍了“2005圣光校友通讯录”,找到了四十多个母亲曾经的校友,尝试着给他们寄去了手写的信,希望得到对方的回信,获得任何关于当年圣光学校的照片或记忆,借此更完整地拼凑出母亲的人生拼图。两个月过去,寄出去的信仿佛石沉大海,觉得穷途末路之际,她收到了母亲在圣光时的闺蜜刘广琴的回信,信中饱含感情地回忆两人在学校的形影不离,一起玩“枕头大战”,周末去母亲歌乐山的家里,吃陈冲的姥姥用自制烤箱烤的面包……在这些细碎的文字里,母亲的过去不再遥远。
后来去重庆拍摄《忠犬八公》,陈冲趁着拍摄间隙,故地重游探访了曾经的圣光中学,学校几易其名,如今是重庆市沙坪坝实验外语学校的所在地。